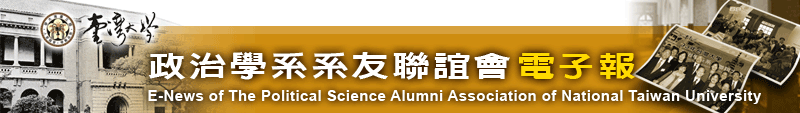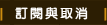只要把自己準備好,其他都不是問題—專訪系友 楊承達大使(63年班)
訪談紀錄、圖 / 傅鈺如 (政研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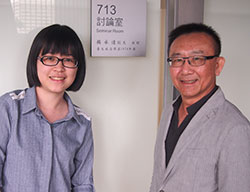
楊承達大使為本系63年畢業,曾任外交部科員、科長、副司長、中華民國駐奧地利代表處秘書、駐紐約辦事處組長、駐布吉納法索大使館參事、駐法國代表處副代表、駐海地共和國大使,現任臺大政治學系「外交實務」課程授課教師(2012年迄今)。
Q: 和您是大學同班同學的彭錦鵬老師,曾在系友會刊中提到您在大學時很早就立定了外交工作志向。您是因為什麼契機,開始對外交事務有興趣的呢?政治系修課上有什麼幫助嗎?
性向、環境及機遇是影響志向的關鍵。對我來說,從小大人就說我口齒伶俐,很適合做外交官,我想這是有影響的。在我們那個時代來講,我們對外交事務有很大的憧憬,覺得外交官能替國家做事,大部分年輕人倒不是以賺多少錢為主要考量,而是在生活還過得去的情況下,能對國家有什麼貢獻。
大學時,我本來是考試分發到台大人類學系,後來大二轉系到政治系國關組時,就已經決定要走外交這條路。那時政治系學生大概有七、八十人,人數並不多,國關組不到二十人,畢業後同組同學去考外交特考的只有我一人,彭錦鵬老師那時是公共行政組的,所以我們那屆只有我們兩個去外交部。政治系的課也都是大二才開始修,得補修大一大概20學分的課,因此我跟下一屆(64年畢業)的同學也很熟,那屆進外交部的有4位,就都是在大學時就認識的。
至於在校修課對日後外交工作的幫助,我覺得人文、社會科學的課程,除了若干專門技術外,大體上是在思想的訓練,並不以職業為導向,在大學裡所受的薰陶可以鍛鍊我們的思考、啟發我們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培養我們對事物綜合判斷的能力。
Q: 這次您慷慨在社科院新建大樓案子捐款了150萬元,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當時的過程?
我跟我的好同學彭錦鵬老師的交情已經超過40年了,我們常聯繫,有時見面、有時打打電話,也常聽他提到推動興建社科院新大樓的事情,所以我對社科院新建大樓的情況是蠻瞭解的。我很佩服彭老師有那樣的想法與毅力去完成一座可維持五百年的基業,同時也找到世界一流的建築師來設計建造,這真的是要有相當大的衝勁與恆心才有辦法做到。我相信彭老師也有不少壓力,但他都能堅持到底,真的讓我很佩服。
我有能力回饋母系,覺得蠻好的。與其他校友的貢獻相較,150萬元實無足掛齒。倒是713討論室還掛了個「校友 楊承達捐贈」的牌子,雖然我知道有這個牌子,但也是今天上來才第一次看到--我希望這牌子別掛太久,希望接下來有系友繼續捐贈社科院一些設備或經費,隔一段時間就把牌子換個名字。
Q: 我記得彭老師也提過您通曉英、法、德三種外國語文,不曉得語言選擇是來自興趣還是有什麼外交需求判斷呢?外派後的當地語言與文化對您有什麼衝擊呢?
我的英文是從初中一年級開始按部就班學習而來,後來到美國喬治城大學外教學院讀碩士,英文當然有些進步。法文則是因為台大國關組必修第二外語,我選法文,修課兩年,略有基礎,直到進了外交部後,有個以西班牙語、德語、法語為主的歐語人才培訓計畫,我報名參加甄選被選上,可以說法語是到比利時跟法國接受訓練時才將基礎打好的。
雖然我的語文專長是英文跟法文,但沒想到第一次外放,反而被放到德語區的奧地利。我在赴任前的三個多月開始自修德語,但抵任時已可在餐館以德語點菜、結帳。我自己學習德語的經驗是,會兩種歐語後,要自修第三種歐語不是那麼困難。很多語言是觸類旁通的,如果只會英文一種外語,可能感覺還沒那麼明顯,因為相對於其他歐語,英語的文法比較簡單,其他西歐與南歐語如法、德、西、義等語言,其名詞有陰性、陽性,乃至中性之別,再加上動詞變化與時態較為複雜,學習上會較英文困難,但學會前述四種歐語中任何一種語言後,由於彼此的語言結構(德語稍異於其他三者)及文法相近,將會增加學習另一種語言的速度。
外交工作基本上是內、外輪調,總的來說,在整個職業生涯,在國外工作的時間會比在國內長,通常是在國內2-3年後派赴國外5-6年,國外工作3年一任,有時兩任都在一地,有時兩任兩地。早年外派地點全由外交部決定,現已可填志願,人事單位以盡量滿足各人的志願為考量。我覺得外交工作本來就應該全世界各地到處跑,沒有絕對好或絕對壞的地方,所以從來沒選擇外派地點,全聽任外交部指派。
另外,關於外交人員的外派還有一項爭論:究應培養區域性的外交專門人才,還是要培養世界性的外交通才?比如說,要培養東南亞的區域專才,那麼一個外交人員可能第一次外放時去泰國、第二次去馬來西亞、第三次去印尼,終其職業生涯都在東南亞區域裡進出。如果是要培養通才,很可就會變成第一次去美國、第二次去波蘭、第三次去約旦了。事實上兩種取向各有其優缺點,我國並無確定看法,因此有些外交人員一直在某區域進出,有些人則遍歷各大洲。
以我個人的情況來說,布吉納法索3年多、法國2年,再加上海地3年多,我在法語區待了大概9年;在英語系國家,主要是在紐約3年半;在德語區國家,反而是在奧地利一待就近6年。我的經驗是,每個地方都不太一樣,即便都是歐洲國家,比利時、法國、奧地利彼此也不盡相同,歐洲國家跟布吉納法索、海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差別當然更大。但對外交人員而言,工作的環境遠比外在的環境重要,也就是說,大使館或代表處內同仁相處的情形,以及我們和當地國政府的工作關係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文化等因素,我覺得人類不分種族,在本質上是相近的,只要「以誠待人」,到哪裡都一樣,至於有人說哪裡的人準時,哪裡的人不守時,我覺得那是枝微末節,並不是真正的差異。更何況現在資訊如此發達,要了解異國情況易如反掌,應該不至於有所謂的文化衝擊了。
Q: 在處理外交事務時,有沒有遇過什麼棘手事件?可以跟我們分享您在執行外交工作的一些故事嗎?
外交事務大概就是兩大塊:一塊是如何促進國家安全及利益,這就包含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另外一塊就是對國人提供服務,包括領務、僑務等。在此或許可說一些平常會發生,但一般人不見得會知道內情的事。
記得我在海地擔任大使時碰到國人遭綁架勒贖的情況。2005年5月海地三勝製帽廠我國籍黃廠長遭其司機與外人串通綁架,該製帽廠在台總公司戴姓負責人獲悉後,從台北打電話來拜託我救這位廠長,並表示無論多少贖金他都會負責。當時綁匪勒贖美金10萬元,我綜合各種狀況做出判斷,為免海地警方介入,如有不慎反傷人質,先後請當地國人及大使館參事(假扮台商)與綁匪談判,幾經折衝,大使館權宜支付了9千美元贖款,黃廠長順利安返。事後雖經外交部請該總公司歸墊是款,戴某人卻置若罔聞,一直到一年後該公司在多明尼加的投資案尚有政府補助款可申領,外交部在撥款前要求他先償還那筆款項,這才把那9千美金要回來。這件事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但經過情形確實如此。
另一件與國人有關的特殊情況發生在卅年前我第一次外派至奧地利擔任三等秘書職務的時候。在1986年左右,有位陳姓國人應聘到奧地利擔任廚師工作,結果在維也納機場出不了關,機場移民局打算將他原機遣返。當地僑民跑到代表處來找我,說該名廚師有入奧簽證,但在機場被卡住了,原因不詳。我當場打了幾個電話,問了機場海關、移民局,也問到奧地利內政部去,但都不得要領,後經移民局同意後,我親自到機場與當事人會面。
進到機場內部,我見到了這位陳先生。據陳先生表示,他第一次出國,經友人介紹應聘到奧地利某城市做廚師,在台灣辦好護照後即依照未來雇主的指示,將護照寄到雇主處辦理入奧手續,其餘的情況他就不清楚了。我一看陳先生的護照內頁,沒有入境簽證,但卻有奧國地方警察局所核發效期一年的居留簽證章。依奧國當時的法令,居留簽證是在入境奧國後,因種種合法理由,由警察局核發,持居留簽證者再次進入奧國國境則不須另持入境簽證。但當事人既未曾入境奧國,亦未曾在奧國駐外使、領館取得任何簽證,又如何能逕取得居留簽證呢?又,在此情況下,如果居留簽證非係偽造,邊境移民局可否拒絕當事人入境?
機場移民局顯然採取了最省事的辦法:拒絕當事人入境。經直接交涉,移民局仍表示愛莫能助,只能原機遣回。我靈機一動,告訴陳先生,如果移民局官員詢問能否自購機票返台,告以身無分文即可,並詢移民局,下一返台長榮班機在三天之後,該局將把陳先生安置於何處。該局官員稱,機場並無暫時拘留處所,陳先生僅能在機場過境室等候下一返台班機。這時我就不客氣地表示,過境室並無任何設備可供旅客過夜,況且陳先生身無分文,三餐都是問題,最起碼應允許其入境數日,由其友人照顧至下一班機返台,如有必要,我國駐奧代表處可保證陳先生屆時離境。移民局官員見我言之有理,不再堅持將陳先生原機遣返,但把決定權推給了奧國內政部。
將各方資訊拼湊後,我大致瞭解了此事的來龍去脈及癥結所在:陳先生的雇主不了解正常入境手續,以為憑居留證即可入境,並藉由良好的地方關係,直接為陳先生取得當地的居留簽證,因此陳先生在本事件中為善意第三人,卻也是受害者,有問題的是簽發居留簽證的奧國地方警察局。基於此一了解,我委婉的向奧內政部官員表示,奧國係以保護人權著稱的國家,但陳先生所受到的待遇顯然不符一般人權標準,如為新聞媒體知悉,恐有損奧國美譽。或許奧國內政部自知理虧,亦恐事件曝光,引發更多問題,不到半小時,陳先生即獲准合法入境。
更有意思的是,跟著陳先生走出海關的還有一個大陸人。原來這位先生在抵達維也納機場前也從不曾出國,但卻持有奧地利駐里斯本大使館所簽發的入境簽證,個中緣由自然耐人尋味。或許奧國內政部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既然同意我國民入境,乾脆把大陸國民一併處理。事後,維也納華人圈流傳,大陸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甚且聘請律師向奧國移民局大力交涉都無法解決的事,一經台灣辦事處出面就搞定了,而且台灣政府確實是在照顧她的國民。這樣的效果倒是始料所未及的。
Q: 以您過往的外交經驗,您會怎麼看待或評估臺灣的外交情勢?
如同前面提到的,外交包括促進國家安全、利益及對國人的服務。國家安全自然是最大的利益,其次為保護僑民、提升國家在世界的形象等。兩岸關係對外交自然會有所影響,甚至可以說,從1949年以來,兩岸關係早已為影響我對外關係最重要的因素。
不同的政黨執政,因其外交政策,尤其是兩岸政策的差異,在外交上的作法自有不同。例如新任蔡英文總統有關「現狀」的宣示與馬英九前總統時期維持現狀的「現狀」是否有所差異?關鍵點還是在是否同意中國的現狀為分裂國家,如果不同意,在外交的操作上自然會與過去8年有不同的做法及結果。
至於一般性的外交作為,不論是各領域的國際交流、提升國際形象的公共外交,以及協助旅外國人、保護僑民等領務與僑務工作,這些都是經常性的工作,不會因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但若干與兩岸政策有關的政策,比如說新南向政策,在外交上自然會投注較以往更多的資源,至於有沒有效果,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過去在外交上的經驗是,重要的外交議題不是涉及兩岸關係就是無法避開兩岸關係,像是推動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等莫不如此。大陸如果加以阻撓,因雙方所能動員的國際力量對比懸殊,我們毫無成功希望;如果我們與大陸妥協,尚可獲若干成果,例如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為大會觀察員。簡單來說,國際社會是角力場所,講的是實力原則,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勢必要有夠多的會員國支持才能進去,要不要與中共妥協是個選擇的問題,不妥協,自然是白費力氣,至於是否能夠藉由外交議題的操作遂行內政目的,那又是另一個問題。
另外順便一提的是,有些人對美國存有幻想,事實上長久以來美國即已表示不支持臺灣參加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組織,在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期間,不論我推動參與聯合國或世衛組織,美國從未支持我國,也從未在表決時投過贊成票。外交重要的議題當然不僅限於參與國際組織,在此僅以此為例,其他的問題應可類比。
Q: 退休後您回到政治系教授「外交實務」課程,這幾年下來有什麼對學生的想法或感觸呢?對有志往外交界發展的學生或系友,有什麼想給他們的建議或提醒嗎?
我教「外交實務」這堂課的初衷,是想讓學生對我國實際的外交工作有多一點的認識,並藉由實際案例的處理,舉一反三,運用到其他的領域。在外交業務上,臺灣現在的做法跟過去比起來進步了許多,尤其在公共外交和對國人的服務方面更有顯著的進步,但這些都與時代的演進有關,例如在1970年代以前,維護我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為我外交重點,1980年代推動實質外交,1990年代推動參與聯合國等,最近這幾年兩岸衝突比較少,所以外交的重點就又不同。我在課堂上除了介紹各時期的外交作為外,並希望藉由一些案例,啟發同學處理實際事務的思維。
這堂課對我的意義是,有機會跟同學們分享一些我過去的經驗,也與同學共同檢視及分析當前的外交情勢及狀況。其次,對我來說,退休之後與社會互動較少,能與青年學子接觸互動,意義重大;年輕人每隔幾年就有一些不同,產生新的想法和潮流,我對這些也不是說全部贊成,但經由與同學的接觸互動,可以更貼近瞭解社會的脈動。另一個感想是,我發現現在的年輕朋友,可能是因為網路氾濫,反而讓同學們書於基本的訓練,例如所作的報告不夠嚴謹,文字、結構都較為鬆散;我想這是值得警惕的,因為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組織與溝通能力,語文不用到非常好,但要能在口頭與文字上清楚表達,邏輯能力自是不可或缺。除此之外,我覺得對台大的同學來說,更重要的是EQ,因為大多數的台大人不缺IQ,但在工作上除了聰明才智外,待人接物更是能否將事情做好的關鍵。
 我想如果同學有志往外交界發展,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個性合不合適,像是喜不喜歡與人溝通?是否願意跟外國人打交道?第二是要瞭解,現在的外交跟我們想像中穿梭於酒會、宴飲、舞會、典禮中,或是時常代表國家上談判桌等是有差距的。談判工作不是沒有,但需要相當的資歷跟經驗才能坐上桌子。許多年輕朋友以為是一考上外交特考,進入外交部後就可以大展身手,最怕的是在這種期待跟實際工作落差太大的過程中消磨了雄心壯志。我想提醒同學,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要有寬闊的視野,長遠的眼光,時時充實自己,腳踏實地,只要把自己準備好,其他都不是問題。
我想如果同學有志往外交界發展,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個性合不合適,像是喜不喜歡與人溝通?是否願意跟外國人打交道?第二是要瞭解,現在的外交跟我們想像中穿梭於酒會、宴飲、舞會、典禮中,或是時常代表國家上談判桌等是有差距的。談判工作不是沒有,但需要相當的資歷跟經驗才能坐上桌子。許多年輕朋友以為是一考上外交特考,進入外交部後就可以大展身手,最怕的是在這種期待跟實際工作落差太大的過程中消磨了雄心壯志。我想提醒同學,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要有寬闊的視野,長遠的眼光,時時充實自己,腳踏實地,只要把自己準備好,其他都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