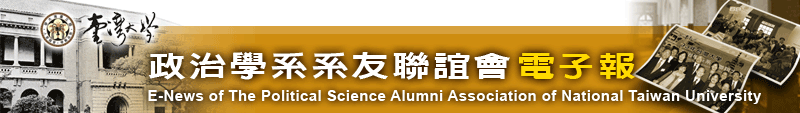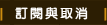江宜樺老師專訪
江宜樺(72年班,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委,臺大政治系教授)/ 楊濟鶴(95級,臺大政治學系碩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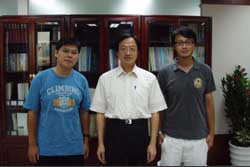
問:老師接掌研考會已經兩個月了,可以先簡單談談這兩個月來的公職生活嗎?目前公職生活的生活型態和之前在學校有什麼不同?平常行程通常如何安排?
這兩個月的公職生活簡單來說就是很忙,但是還沒有忙到讓自己的生活步調整個亂掉。我常常對人講,我現在的工作量大概是之前的十倍。以前在學校的生活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接學校行政工作之前純粹只是教授的階段,另一個就是擔任社科院副院長,後來又擔任台大副教務長,前後總共四年的階段。
純教授的階段很愉快,唯一的壓力來自不斷地備課、作研究、發表論文。接了行政工作之後,其實行政工作佔掉很多時間。擔任副院長佔掉將近一半的時間,擔任副教務長佔掉三分之二的時間。因此在擔任行政工作之後,我的備課和學術研究就已經受到影響。原本是希望今年七月在學校行政工作告一個段落,研究休假一年,然後回復純教授的工作。後來因為政府改組、劉院長力邀的關係,生活的計劃作了蠻大的改變。五二0來這邊之後,工作數量和密度大概是我在學校行政工作的十倍。以前擔任副教務長,我的教學發展中心有三十個同仁,現在的人員則是十倍,業務量和公文也是十倍。以質來講,以前教學發展中心一年的預算是接近三千萬,現在批的公文可能一件核淮的經費就是三千萬。
以前我的行程都是自己安排,我答應了的行程就自己寫在記事本上面。現在我的行程則是改由秘書來安排。通常會接到很多電話,有各種單位的邀約、參加研討會,致詞,或是院本部臨時要開協調會議。這些行程和開會通知不斷,我不可能自己接電話來過濾行程,決定要不要去。我就請我的秘書來過濾。像是一般民間團體或是學校邀請演講,她會告訴我,我就會婉拒。真正需要參加的會議,像是院裡面的會議,或是和別的部會共同審查的會,那麼我們就要想辦法把行程排出來,我在研考會裡面每個星期平均至少會有五六個會議,像是業務會報,組織改造推動小組的會議。這些不同的會議和行程,她都要想辦法幫我排進去。我每天回家的時候都會拿到更新的一週行程表。
問:老師所受的專業訓練是政治思想領域,現在接掌的研考會的性質卻偏向公共行政領域,不知道老師接掌研考會之後,對於這兩個領域的差異是否有什麼特別的體會?這兩個領域的從業人員的思惟方式有什麼差別?
我想你們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做得來。大家會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在答應到研考會之前也問過這個問題。內閣要找一個研考會主委,為什麼要找我,因為通常會找公共行政、公共政策的學者。研考會往來的學者也多是公共行政類的學者,因為他們作公共政策的研究、計劃、考評。但我來這裡之後發現,其實還真的不一定要找公共行政的學者。找公共行政的學者,顧名思義,好像就找到專長最吻合的專家。但是研考會的職掌和任務,坦白講是遠遠超過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它屬於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部份當然佔了很大一部份,我們要作公共行政和公共政策的研究。比如說台灣是不是要開放觀光賭博產業,又像是性工作是否要除罪化,我們會作研究或是妥託學者作研究。我們在這裡不可能研究柏拉圖或是韓非子。我們也作民調,就跟洪永泰老師作的一樣。因此就法定職掌而言我們和公共政策比較有關。
公共政策思維的特性,就是評估一個政策到底要不要作,在什麼時程推出,它有什麼該注意的地方,在執行的時候如何管控,執行完畢如何評估。但研考會有些事情是遠超過這些部分。從角色界定來說,他其實是行政院的幕僚機關,像人事行政局、經建會、主計處等都是直屬行政院的機關。內政部、教育部、農委會、勞委會那些大部會,他們有特定的服務人口群,有比較明確的業務職掌,作政府為民服務的直接工作。但是幕僚機關是幫院長作全盤的思考和協調工作。像是研考會是思考整個政府應該要作什麼。整個政府作的就不只是公共政策,比如新政府上來,有中長程的四年計劃、包括我們國家是否要推動憲法改革、要不要推動整個行政院組織的大變動、或是行政院和立法院之間的關係。行政院各部會和執政黨黨團的關係。研考會思考很多行政院的整體的大政方針。這遠遠超過一般說的公共行政,各部會的施政叫作公共行政,如果是思考整個國家治國的藍圖的時候,這不僅是公共行政,這就是我們政治學所說的政治。它比較接近柏拉圖所說理想國,或是霍布斯所說的專制主義國家。這其實是相當高層次的東西,研考會是以院長的幕僚機關來提出這些東西。就這個角度來說,我倒是覺得非常可以和我所學的呼應,雖然做這些事情我不會提哪個思想家說了什麼,我們在公部門不會使用學術語言。但是政治學的原典和經典所吸收到的東西,在做這種治國藍圖的時候是極為重要的。如果我只是學公共行政和行政法,是不可能作好這些事情。所以要看你怎麼界定研考會的性質。如果把研考會拉高到治國藍圖的層次,這就是政治學。
問:老師之前除了研究和教學之外,也曾發表關於轉型正義、教改等議題的社論。不知道現在的職務和過去自己所關心的議題是否有產生交集?或許老師認為是否可以透過現在的職務來實踐自己對於這些議題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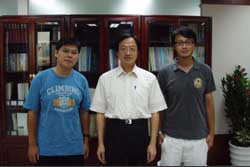
我想每一個願意從學界到政府部門服務的人,多多少少都會想要透過職務來實踐自己的想法,像勞委會主委或經建會主委,這點是無庸置疑的。倒是說你所在的職位,是否能夠讓你名正言順去處理你所關心的議題,這是另外一回事。我在還沒有到研考會之前,也關心過像是頂尖大學、樂生療養院、無住屋者的問題,我關心的問題其實很廣。但是政府機關的職掌是有限定性的。所以比方說教改,是教育部部長主政的問題。研考會主委就不宜像過去學者去批評、檢討教改。又像是以前我對樂生療養院有一些想法,但是現在樂生療養院的主政單位是衛生署、內政部。我當學者的時候是什麼都可以批評討論,但是現在是內閣特定部會的主管,把自己該管好的事情管好,那就是盡本分。
非你職掌的業務,你的關懷倒是可以透過兩種管道去表達,你有很多機會和這些部會首長見面,可以用非正式的方式來交換你的理念,就不會說大家在民意論壇見。另一個管道是透過正式的行政院的院會,所有重大的法案和計劃要送立法院之前都會提到院會上來討論。這個時候如果你以前對於該法案有關心,你可以提出來,因為這是院會,所有部會都可以討論。但是院會的時間很短,不像學校開個學術研討會,用一整天時間在討論社會福利問題。院會可能只有兩個小時,有三四個法案要討論,每個法案只能大體上討論一下。所以我們會看時間允不允許,把自己的意見表達到某個程度。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像學者一樣投書或是罵政府,我們現在就是政府的一部份。你自己該盡責做好,而不可能又想掌握政府權力,又可以像學者跑出去外面罵政府。我想天下沒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問:老師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糾葛和分際,其中有提到參與公職可以是法政學者實踐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可以請老師再為我們談談學術與政治糾葛和分際的問題嗎?
在那篇文章中我認為學術與政治有一種糾葛,而我們從政者要想辦法畫分分際。參與公職當然是一個法政學者去實踐他的理想和社會責任的一個方式。但是這種方式,比起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寫文章評批公共事務,是很不一樣的。一旦進入到參與公職的層次,這裡面的分際的掌握,的確和一個純知識分子不同。我記得龍應台曾經講過,知識分子的武器或說是權力是來自於她的筆,她沒有什麼實權,可是她可以用那支筆來發揮蠻大的批判力量。但是她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之後,她決定暫時封筆,因為她不能讓這兩種角色混淆,她過去對文化事務有很多看法,可是今天變成台北市的文化局長之後,你現在就是作給別人看,就是換你被別人批評了,你要讓別人看,文化事務如果落到你的手裡,你會怎麼做。同樣地我現在到了研考會,研考會比較有關的職掌,比方說行政怎麼革新、憲法修正要怎麼推動,我現在有機會去做。以政務官的身分,去負責把相關的事情弄清楚,然後一步步推動,看它完成。這已經不像一個學者,高興就講,講了就跑,講完還有別人講不同的意見,我不負責,我已經講完就好了。我講的意見很可能只是片面的意見,但我假定別人有別的意見,大家都在公共論壇講一講。我們現在變成彙整所有意見然後把它變成方案加以推動的人。這時候韋伯說的責任倫理,在這個身份上就顯得特別的重要。一個學者一旦變成政務官,他的學術訓練自動變成為他從政資源,他也喪失了成為一個獨立批判的公共知識分子的特權。他成了決定政策,並且為政策負責的人。責任倫理會使得我們變得比較務實,比較謹慎,這是一定的。當學者的時候你可以很理想化地說,什麼事情就應該怎麼做,因為這樣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但是你當了政務官之後,你要去處理這麼做之後所有的後果與代價。例如對於河川地住戶的拆遷應該給予相當於中產階級的公寓才算人道。可是你真的面臨拆遷的時候,你要看政府一年到底有多少預算,這些預算你不可能全用在拆遷戶的補貼。可能你最後定出來的標準,會是你當知識分子的時候所不滿意的標準,可是你現在作個政務官,你必須在部會有限的預算下去執行某個政策,然後還要照顧到其它的事情。這時候你就要很負責地去分配這個預算。你如果是知識分子你會不滿意,但是你是政務官,必須妥善分配資源。而不是把所有的資源用在你關心的項目上。這就是最大的、要掌握的分際。
問:不知道老師對於接下來幾年,在學校的研究和教學的規劃為何?這也是很多學弟妹,不管是需要找老師的碩士班學生或是要修必修課的大學部學生所關心的問題。
這牽扯到我會做多久,我目前向學校借調的簽呈是寫兩年,但那沒有什麼太大意義。因為你如果做得會比兩年久,兩年之後會再上個簽呈。但是如果因為內閣改組或是做得很不順利,與官場不合,隨時可以提早回去,三個月半年也是有可能。大部分政務官沒有任期保障,也不知道到底會做多久。當我寫兩年的時候,是希望大概兩年之後工作告一個段落可以回學校。假定說我做兩年的話,這兩年中在學校裡面會維持教一門課。我跟系主任討論過,最好不要教大學部的政治哲學,因為人多,調課也不方便,我現在做政務官,很多行程都由不得你自主。因為上面還有更高的政務官。像院長今天去左營運動選手訓運中心,給我們的選手打打氣。昨天通知我今天本來是要跟去,但是因為和各位有約,所以我就派了另一個同事去。否則我今天臨時就去了。政務官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行程。傍晚秘書長如果要和我談治水的預算,我就去了。雖然我傍晚可能本來想跟小孩子一起吃飯,我還是去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學校的教書一定會受影響。最好不要教必修的大班課,就像許多學校的老師借調的時候,就只教研究所的課,如果能夠教選修最好,如果是必修的話就要控制人數,時間調到傍晚五點到七點,這樣就不會影響到公務。其實每個學期還是要開一些必修課,我們的老師有限。我下個學期是開西洋近代政治思想專題。我現在還在想我要讀什麼原典,這個我有在準備。人數最好是十個人以下,影響到的學生越少越好。大學部的西洋政治哲學兩年內不會開,由本系陳思賢老師合班來上課。其實本來我九十七學年度就是研究休假,就講好是陳思賢老師帶。這就像上一次他出國,是我在帶一樣。現在的差異就是可能他不只要帶一年,可能要帶兩年。我也跟系辦建議,如果陳老師覺得壓力太大,需要單雙號分班的話,到時候會建議系上聘一個兼任老師。
問:最後可以請老師對有志於從事公職的臺大政治系學弟妹,尤其是政治理論組的學弟妹,說一些話嗎?
我前面其實也講過,我自己念政治理論的心得,從來沒有認為政治理論是抽象、空泛、沒有用的東西,我從年輕的時候就很喜歡念政治思想的東西,也一直認為政治思想的東西是極為有力的。在不想致用的時候,可以只關在書房,寫東西寫個五年十年。可是當要用的時候,可以在很多大政方針上發揮其用途。我目前從政兩個月,深深地感覺,我這個想法是對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我要處理的事情都是蠻高層次的事情。我們談的都不是行政的事情,而往往是政治學最核心、最根本的的事情,包括國家存在的功能、政府的職責分際在哪裡,有多少核心部會必須存在來做這些事情,又有多少政府在做的事情應該要交給民間、行政院和總統府、立法院的關係。行政院在國會接受反對黨質詢的時候,不就像政治學所講的敵友的對抗嗎?我們最清楚史密特所說的敵友對抗或是馬基維利所說的爭奪、戰鬥。落實在實際的政治,你就可以有各種應對它的可能性。又比方說自由主義所說的理性溝通,共和主義的人所說的訴諸於國家的熱愛、團結,以及現實主義所說的人性本惡。政治學所說的很多東西都是活生生的在真實的生活裡面。
這些絕對不是研考會三百個同仁的考績怎麼打或是放假和薪水的問題,政務官思考的是高層次的問題。以勞委會來講,國民年金法已經通過,我們進入全民保險的時代,這是幾十年來沒有做到的。福利國家的時代來臨了。如果我是勞委會主委,我就會面臨兩個問題要處理:不同身分別的人有不同的保險制度,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第二個,國家承諾要照顧老百姓,給他們年金,可是你財政的長期負擔可能會有問題,你又不能大幅增稅,財政的赤字會越來越大,過了十幾年之後可能會破產。那麼請問你要怎麼辦?像這種問題,牽扯到社會正義能不能落實,福利國家到底能不能長期運轉,自由主義的某些理念也要受到檢驗。我覺得學政治理論就是思考這些問題。如果一個人沒有學政治理論,他只學過國際關係或者是經濟學,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處理這些問題。到了最核心的基本價值和治國藍圖的問題,政治理論所發揮的力量最大。遇到最強悍的問題的時候,政治理論發揮的力最大。反而是有關小細節的問題,像是報帳核銷等等,它一點用都沒有。因此學習政治理論的學弟妹一定要對自己所學的東西有信心,在他們處理越高層次的事情會覺得其用無窮。
如果沒有打算從政,那也沒關係。沒有機會去實踐,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有用,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書房裡或是圖書館得到知性的滿足。因為你是不斷和一流的古人對話,像是馬克思、黑格爾、柏拉圖這些一兩百年才會出現的人。讀他們的東西和他們對話、向他們學習這件事,本身也是很愉快。如果有一天你離開書房,從科員開始做,做到處長。到了處長實踐力就已經很強。一個處的預算大約是八千萬,八千萬給你,你要做什麼已經是很實際的問題。學政治理論的同學,看起來似乎是考高普考最沒有機會的,所學的東西也是看起來最虛無飄渺的,所以會擔心所學的東西沒有用,畢業之後怎麼辦。畢業之後大家都是從最基礎的工作作起,你可能是國會助理、小科員、或是到私人企業當業務。沒關係,那只是個起點。慢慢你進入你的中年之後,你會做到中間層級的職務。如果你的際遇或是你的能力使得你達到決策的層次。那你就更能夠體會到,我們所學的東西,比起很多零零碎碎的技術性東西來得可貴太多。一個國家的領導階層,就像總統、院長,如果沒有學過政治理論的人加以輔佐,其實這個國家很難能夠治理得完善,政治理論就是講這些最高層級治理的問題。我要對學弟妹講的就是,大家要對所學的東西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