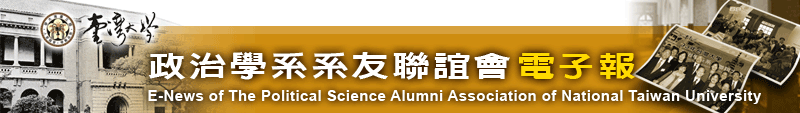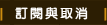政治學的碩學鴻儒:緬懷任德厚教授(1941-2020年)
詹康教授(政治大學哲學系,77年班)
一、行述與學術
任德厚教授是將門之後,外公張楚材,湖北天門人,光緒六年(1880年)八月廿四日生,1905年張之洞選派赴日本讀書,改習海軍,娶有馬柳子(華名張慕真)爲妻,後追隨同鄉兼同學沈鴻烈,創建東北海軍,積功晉陞代將。民國26年12月青島陷於日人之手,楚材公脫離軍界,38年隨女兒女婿定居高雄左營,每年春節昔日學生自海軍總司令馬紀壯、劉廣凱以下將校官拜年賀歲,絡繹不絕,戶限爲穿。56年2月13日去世,年87歲。
外婆張慕真,本名有馬柳子,1886年生於日本山口縣,長於東京,私塾補習教育畢業,擔任小學教員。嫁予楚材公後,飽歷戰亂、播遷、仇日、赤匪、病魔、丈夫牢獄、子女殞喪之悽苦,因皈依基督教而堅忍不移。晚年各種事奉天主的工作無不竭力從事,感召廣大信徒,在南、高、屏教會備受尊崇。民國68年10月21日去世,年93歲。
父任毅,四川銅梁人,光緒廿四年(1898年)五月四日生,民國13年煙臺海軍學校駕駛班第十五屆畢業,是楚材公的學生、部屬、女婿。抗戰時期脫離軍職,在威海基督教私立育華中學當數學老師,戡亂時期復職,歷任海軍教導總隊大隊長、九華軍艦艦長、海口巡防處處長、海軍官校船藝系主任、海軍針織廠廠長,46年以上校退役,復於高雄水產職業學校、高雄海事專科學校(同校前後校名)兼課。89年11月6日去世,壽102歲。
母張志超,1909年生於日本東京,自幼習鋼琴、小提琴、口琴、西式水彩,畢業於美國教會興辦的煙臺私立衛靈女中,民國17年與任毅公結婚,生育三子四女。創辦左營自勉幼稚園,擔任園長,能唱、能畫、能編、能舞,50歲退休。是有新式思想的才女,然常屈於丈夫而不能實現抱負。民國70年2月19日去世,年72歲。
先生民國30年9月26日生於山東威海,在七子女中排行第五。8歲來臺,長於左營。二位哥哥皆就讀臺大電機系,先生獨對國事國運有濃烈關懷,入臺大政治系,轉法律系司法組,54年學士畢業。服兵役時,擔任三民主義巡迴講習教官。役畢,入臺大政治系就讀碩士班,同時考取公費留學獎學金(公共行政類別,見56年7月18日《聯合報》),57年肄業赴美,59年取得美國長島大學政治學碩士,尋進入紐約市社會研究新學院(先生譯爲新社會科學研究院),公費獎學金結束後由臺灣父母和留美兄長匯錢資助其學業,並在紐約世界日報社工作(65年2月起發行)。64年結婚,67年春生女,同年夏以《The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5: Law and Politics in Taiwan》(1949-1975年中華民國的憲政發展:臺灣的法律與政治)論文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由袁頌西主任聘入母系,執教凡27年半。95年1月退休,投閒置散,一無正兼職事,二無開會演講,三無交遊聯誼,唯以書城圍繞,求知自娛。102年師母中風,先生獨任照顧之責,盡心竭力,督導師母復健,七年來成效羨人,見者無不讚嘆。先生素無大恙,今年7月13日外出買飯盒,因天氣炎熱,而他人已腸胃不適數日,突然心跳急速,無力舉步,坐在公園喘息二小時。踰二日在家跌倒,左額捽破,赴仁愛醫院縫了五針,再踰二日即7月17日,在家溘然長逝,享年78足歲。

先生生具一對大眼睛,同學稱爲「任大眼」,自幼便擄獲長輩與平輩女性芳心。及長,嗜閱報章雜誌,泛覽政論時事,熱衷國內與國際議題,討論起來滔滔不絕,評析意見層出不窮,且富有領導才能,精力無盡,活躍於學生羣中,鋒頭極健,而對自己的生活視爲瑣事而不足介懷。入大學後,發生雷震組黨事件,而知識界繼起的力量並不間歇其啟蒙的腳步,先生在校,擔任健言社社長、大學論壇社社長、學生代表(據說擊敗俞寬賜老師)、學生運動「中國青年自覺運動推行會」顧問,對原本以文藝創作爲主的《大學論壇》,加入社會科學、國際法、人文學的文章,是爲該刊物蛻變之始。
先生大三,除擔任社團社長,復參加慶祝總統華誕的演講比賽,題目是「從世界歷史看中國自強之道」,因他平日對此題目已常在思索,一講便不能自休,比預定時間超過了一倍半,以時間控制不當,落得第二名。又復膺選爲52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青年代表,與蔣中正總裁及八百五十餘位國內、海外、敵後代表同堂開會。先生自言他曾對中華民國三位總統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直言國是,是他一項記錄。先生開會建言,當時大學的三民主義課程,與現代的社會科學有了相當的距離,如何使今日的社會科學融貫進入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中,是爲教育的當務之急。先生後來授課,從憲法學角度評議孫中山五權憲法思想(與五五憲草)之不當,推許政協十二原則與張君勱主筆的政協憲草,其發軔即在於大學時代學習社會科學與法學,體認社會科學的重要。
大三上學期先生在校內外的鋒頭正旺,然而卻在此時,他做了急遽的轉向,決定更用心於閱讀歷史與政治,並退出學生活動。他說:「在兩年來的大學生活中,我發現自己對實際工作的能力比較缺乏,因此希望將來在畢業後,能留在校中從事學術方面的工作。」因此辭去大學論壇社長職,停止發表閎言崇議和與同學高談闊論。先生從嗜好讀書而終於發現了黃金屋,感到從科學的角度理解現實,從歷史的角度追索宿因,其魅力更勝於關切心急與立言暢論。知與行都有足夠的時間,那是最好,可是當求知的時間大增,實行就需要擱下了。

留美第三年,爆發保衛釣魚臺運動,嗣後臺灣留學生分裂爲左右兩派,激烈論戰與組織運動的經驗有效培訓了這一代學子的政治能力。而國際風尚自六○年代外國知識青年向左傾,到七○年代外國政壇人物也向左轉,周恩來的一顰一笑,吸引了最大的國際視聽,臺灣的國際地位愈走下坡。先生在紐約適逢其會,然而維持自己既定的路線,似乎並未投入這場盛大的愛國運動,與串聯學生以對抗左傾勢力。美國與臺灣的保釣健將,多是臺大《大學論壇》先生的學弟,而此時先生則似乎不在他們的人際網絡中。先生對其留學生涯覺得可足追憶者,唯美國老師封以「小蔣介石」綽號之趣事。蓋美國人對臺灣的概括印象是蔣介石獨裁統治,而先生研究臺灣憲政,比他人更明瞭臺灣在政府組織和運作上努力落實憲政,而行政院的提案在立法院不照章通過者所在多有,此見令美國人大感新奇,故又以爲先生是國民黨代言人而諧謔之。
歸國任教後,僅零星應邀座談,與應邀撰寫少量時論文章,不曾主動積極發表言論影響社會觀念,也不曾出外活動引領社會進步。當時,臺灣社會開始形成了集體感受,期望各方面都應進行更大改革,許多歸國學人一秉忠藎熱忱,學以致用,批評政府,提出進步觀點,催化改革速率。值此知識可以帶動變遷的歷史時刻,先生卻沈潛於學術,默坐於象牙塔,對著愈來愈大的改革浪潮,冷眼看它而不與其他人並騎著浪頭,灌注它能量,指揮它方向。先生深信:「爲了看清楚一個東西,必須抽離,和它保持距離。」先生研究政治發展,身在臺灣各方面發生急遽變化的歷史階段,選擇了隔著距離研究它、理解它。先生還說:「人有理想性雖好,但有現實意識也很重要,殷海光就是現實意識不足,而胡適能兩者兼備。」體會先生的意思,是不侈言改革,而應同時體察時局,估計衝撞權力的勝算,時機未到時願意承認。再推而言之,瓜熟蒂落時少我一人亦能成功,時機未到時多我一人亦爲徒勞,則默坐靜觀,做一天地間閒人可也。
黨國倚重學者以治國治黨,而本系人才薈聚,屢獲當局器重。先生早在學生時代便嶄露頭角,成學之後卻從未有一官半職,我嘗詢問先生,政界必有一種人專門往學界物色人才,應無不識先生這塊美玉之理。先生曰否:「他們最善於辨人心志,如果他們察覺你無心,他們不會開口。」然而先生無意仕宦,除了因爲一心只在學術,應還有別的考慮。我曾向先生提起某位普受敬愛的學者,他寫了某科目的必讀書,又官位崇隆,對國家卓有貢獻,不料先生說:「我鄙視這個人。」先生對其人有何劣蹟決不鬆口,我扣問再三,他最後說:「在有些條件下,有的人守不住。」故先生當亦有見於從政與道德清白不能兩全的情形,爲潔其身而不得不廢君臣之義了。
先生在大學部開設當代政治學理論與批判、政治學、中國政府、中國憲法與政府等課,在研究所開設比較行政、比較政治專題研究、比較政治理論、政治制度論、比較民主政治、比較憲法、國家安全專題研究(與張劍寒教授合開)等課程。鑒於本系學生將來都是政府與社會的高級人才,故授課兢兢業業,全力以赴,務求內容之充實完善,講解之效率明淅。在課堂上從不談當週時事,不臧否人物,避免拿臺灣做例子,一切分散焦點之事皆所不爲,只傳授知識本身。如果問他對政局或高層政治人物的意見,他會回答:「我雖然拿到博士,但在這世界上,我不知道的,比我知道的還多。」在先生而言,對個別人與事的評價並不是科學知識,只能供做茶餘飯後的談資,不爲其所尚。講課中間,每要突兀停止一個話題,先生會用「anyhow」截上啟下,這個新鮮的英文字遂成爲學生對先生的標記。

先生著書三種,《國家、系統論,與政治過程:比較政治學理論取向之研究》(民73年)是先生升等之作,探討政治學從行爲主義轉變到後行爲主義中間,系統論和國家理論(國家與社會互動)這兩種理論的優點如何可以結合,與避免偏失。本書的研究奠定了先生後來治政治學的綜合性取向,將兩種理論典範都發揮到最大效用。例如在總統制與內閣制的選擇上,即使學者多數傾心內閣制,先生卻基於我國原有「國權傳統」,而內閣制是社會將國家吸收而形成的政制,故斷言內閣制很難爲臺灣政治領袖與人民所接受,學者的偏好很難感染到社會多數人。
先生自從承擔「政治學」教學任務,即開始撰寫課本,每年將已成的各章鉛字排版,印發給學生,到民國81年完成全書,寫作超過十年。先生《政治學》的最大特色至少有三:第一、二十世紀政治學經歷了從國家學到行爲主義、再到後行爲主義的轉變,先生以最後發展出的新制度論向前統攝,將這三種學術典範的知識成果融於一爐。第二,先生有比較政治與政治發展的學養,所以書中所論的不僅是成熟國家的政治情形,還有不成熟國家的。第三,全書字數較多,且後來增訂七次,到民國97年第八版才停下,書本愈發厚重。由於語句要言不繁,所以知識量非常大,這必須感謝那時的制度不要求教授拼論文,所以先生得以爲了課本的完善而廣泛閱讀,濃縮整理到書中。這本《政治學》是殫精蘊思、再錘再鍊的持續性創作,以心血的灌注而論,是先生最重要的著作。而以架構之龐大、內容之廣博而言,本書已不只是課本,而有點百科全書的意味。以我所知的中英文政治學課本,皆無如先生所著之淵博該贍者,此課本實奠定了先生乃是政治學的碩學鴻儒之身分。
先生與本系呂亞力教授兩位的《政治學》課本,從1992年至大約2005年前後,是臺灣政治學課本的兩雄,讀者不只是各校政治相關科系學生,還包括相關研究所考生與相關高普考考生,與對政治學有興趣者,人數可能要以十萬爲單位來計算。而先生之書紮實精深,學子尊崇爲聖經,先生之名亦因而大行於世。
第三書是《比較憲法與政府》(民91年),本書對《政治學》相關部分做了擴大說明,在局部意義上也可視爲繼承薩孟武《政治學》之作,先生曾兩度受業於薩孟武教授,故以此書做爲紀念。此書的風格一如《政治學》,展現作者的博學,與系統化、類型化的能力,所以知識量雖大,而駕馭有餘。以下我想揀先生對臺灣的意見稍做陳述。
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後,憲法在李登輝總統任內增修六次,在陳水扁總統任內增修一次,先生批評增修結果說:「五十分都不到!四十分都不到!三十分都不到!二十分都不到!」我曾持此意見詢問蔡政文老師,蔡老師回答:「憲法並沒有修得不好;是他們不遵守!」此言指陳水扁讓立法院少數黨組閣,與先生的憲法學角度完全不是一回事。先生認爲增修條文不及格的理由,今只可從其書略窺一二。增修條文將立法院對行政院長提出不信任案的立法委員連署人數訂爲三分之一,書中認爲太高,不利於政策辯論(頁351)。又規定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而未規定此時行政院長應將職權交給副院長代理,會發生兩個職權由同一人行使的情形(頁435-436)。
八月甫就任的監察院長陳菊表示希望監察院能廢除,最後我想略敘先生對監察院的修憲構想。監察院的原始制度,是由省市議會選舉產生,並有同意考試委員與大法官的權力,所以先生認爲監察院除有中國監察御史傳統之淵源,尚有國會上院的特徵(參見頁242)。據此,先生主張使它成爲真正的國會上院,這樣一來,兩院制國會可以依兩種民意基礎選出,反映臺灣社會的複雜構成狀況,而立法權與監察權不致分離,也能有效監督行政權。然而增修條文廢除了監察院的民意機關色彩,只保留中國監察御史傳統,雖然遠離先生的構想,可是先生書中的比較憲法知識,足供我們思考監察的未來。書中說:「社會構成較爲複雜的國家,則需要兩院制的程度必然較強。」(頁278)以臺灣有閩、客、外省人、原住民、新移民等幾大族羣而言,或以臺灣北、中、南、東部的差距而言,都是可以適用的。書中又說建立兩院的一種可能目的是「抑制下院」(同頁),這也可能得到今人認同。
二、師生緣
我沒有繼承先生的學術專長,只是一名修課的學生,卻與先生結下36年的師生緣。
一、修業:民國73年大一,上政治學必修課,始受業於先生。先生講課用了很多翻譯來的動詞名詞,很抽象很生份,我卻很聽得懂,就這樣我變成先生的粉絲。大一新生能遇到學問令他折服的老師,隨他進入由學術語言所構成的宇宙,就在理解和識見上也轉大人了。每人都有不同的師生緣,我的同學喜歡吳庚老師的詼諧、莊錦農老師的尖銳問題、許介鱗老師的樸拙,而我獨愛先生傳授知識的「複雜」(sophistication),政治系老師有兩位讓我學到最多東西,另一位是「比較政府」的魏守嶽老師。我喜歡先生的課到這種程度,是大二上了吳庚老師的「中國憲法與政府」(胡佛老師當年休假,致本班未受教於胡老師),大三又去旁聽先生的「中國憲法與政府」一年,因爲「政治學」和「中國憲法與政府」是先生在大學部僅有的兩門課。研究所考試的「中國憲法與政府」是先生出題,放榜時先生叫住我說:「這科考95分的是不是你呀?」但那天我還沒回家看成績,不敢承認下來。謝師宴的主辦同學託我邀先生到席,因爲知道我們熟稔,而先生也大方賞光。我將負笈美國,先生請我到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吃自助中餐,爲我踐行,現在我師法他,也對即將留學的學生踐行。

二、愛情:班上女同學王綉雯,比較喜歡和男生玩,我和她和另幾位同學常在一起。先生看在眼裏,對我講了不下三次,覺得我和王綉雯滿登對,要不要追追看,我回稟他:「王綉雯說過不考慮我啦。」碩士班指導老師孫廣德有三個女兒,老大結婚,老二、老三是雙胞胎,單身,先生就問我:「孫老師想不想把一個女兒嫁給你啊?」我不得不糾正先生,因爲孫老師是儒家式的君子,腦中絕對沒有這種想法。這叫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吧,真是的!我以先生爲鑒,會等學生告訴我他們喜歡誰或喜歡什麼條件,不會不弄清他們的喜好就亂給意見。但先生看我一直不交女朋友,而爲我心急,我亦能感受。
留學在外,認識了女朋友及未來的妻子,終於不必被他關懷了。學成歸國,帶未婚妻晉見先生,未婚妻也修過先生的政治學,先生大喜過望,因爲他所教的學生嫁娶了他所教的學生,是一件喜事,也是兩件喜事(加起來是三件喜事?我們算術不好……)。他請我們到「大聲公」二樓吃飯,三人點五道菜,我連說點太多,他說不用怕、絕對吃得完,結果吃是吃完了,但是是靠我吃撐了。他不參加婚宴,但專程來簽名,留了紅包。生子以後,帶兒子向先生拜年是先生最高興的事,我要給他拍照他不讓我拍,但與我兒子合照他就很樂意的端正坐好。
三、先生的書:我向先生討贈他的升等書《國家、系統論,與政治過程:比較政治學理論取向之研究》,他進房拿書,解釋說有一本封面已題贈給同事,然後自忖這麼做無何意思,便沒送出,但也不宜給我,所以把封面撕掉有題字的半頁後送我。年輕時臉皮不厚,現在的我就會施展軟功,讓先生將撕下的一半封面賞出來,我黏回去,還書籍一個完整的門面。禮俗失去情意交流,空留形式以後,的確令人的良心發生遵行與否的猶豫,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先生重心意而不惜略爲失禮。
《政治學》經過十多年撰著,在民國81年問世,書稿是手寫後再交付打字,先生說錯字很多。我校對一遍給他,他很歡喜收下,再拿一本給我,說:「一本換一本。」次年我碩士畢業,論文題目是《明代的教化思想》,他覺得題目就是政治社會化概念,便寫進《政治學》課本的註釋裏,推薦大家讀。他對我說:「課本該要有一章寫政治思想和意識形態,可是我怎麼讀都想不出如何寫進去。」我說所有的課本都有這麼一章,先生的不可沒有,然後我就揣摩怎麼從實證政治學過渡到規範政治學,寫了二、三百字的引言給他,如果說得通,先生就能接著寫下去。但屢次增訂再版,這章終究還是闕如。
民國86年值香港回歸前夕,啟德機場陳列《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精美小冊供人取閱,因先生研究憲法,遂攜回一本送他。

四、師母中風與康復:師母在上班機關裏綽號「女超人」,突罹中風,聞者皆覺不可置信。我告訴先生有個著名的TED演講,是研究神經科學的Jill Bolte Taylor觀察自己37歲發生中風的幾小時經過。她的書《奇蹟》包含了更多醫學知識、她對醫療方式的看法、與八年復健的做法。先生說馬上去金石堂,而且要買兩本,一本送給醫生看。隔年我問他,他說這本書給的最重要觀念是一切對大腦都是可能的,我補充兩點,一是需要時間,因此愈年輕中風,恢復的本錢愈夠,二是需要知道受損的機能是什麼,以施予訓練。
先生說住護理之家,有錢多做復健,和沒錢少做復健,就造成結果天壤之別,言及社會貧富差距,甚爲感慨。
先生對師母的復健練習,極爲嚴格要求。師母的雙胞姐姐對師母常常不忍要求,先生說:「這樣是繡花拳,沒用。」
先生說,他對師母說,他只能照顧師母到75歲,以後就不敢講了,所以師母一定要努力康復。
五、語錄(補充):先生一家,自阿姨影響外婆信奉基督教起,至先生已第三代。先生是沒有回去教會的基督徒,他自我反省說:「當一個人讀書思辨到某種程度,就會發現很難再相信宗教。但是話說回來,能相信宗教的人才比較有福氣,不得不羨慕他們。」
先生說:「老蔣成也因他的性格,敗也因他的性格。」
先生說:「王文興《家變》就是寫小蔣,這非常明顯。」
先生退休,深居簡出,連本系動態亦不復與聞。我帶一本小冊給他,他翻開發現是吳庚老師哀思錄,連呼:「啊呀!啊呀!」
六、結語:從73年到109年,我一共做了先生36年學生。雖然還有母親,還有一位敬愛的指導老師,比先生大一歲,還在國外大學崗位上,但是先生突然離世的噩耗讓我悵惘良久,在臺灣的男性父執輩可以給我孺慕、給我智慧、給我批評、給我揶揄的從今就沒有了,我變成最上一階,只有對下的關係了。謝謝他接納一位按他的說法是「有點呆頭呆腦,做讀書的工作還好,做其他工作都不適合」的學生,關懷他的求學、職業、婚姻、家庭36年。
我想過先生百年之後,我可能要爲他立傳,然因先生平常樂觀以與父親任毅公102歲齊壽爲目標,故有太多的事我沒及早問他,每次與先生會晤,不少時間花在關懷我的近況和閒聊近事。我幻想爲先生寫篇思想性傳記,交織他的成長與時代變遷,做爲一個受業學生送他的最後禮物,這個機會現在已經永遠喪失,僅能以此不完整的文章與系友一同緬懷這位啟蒙我們政治學的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