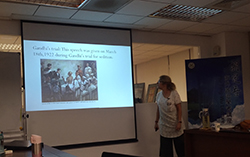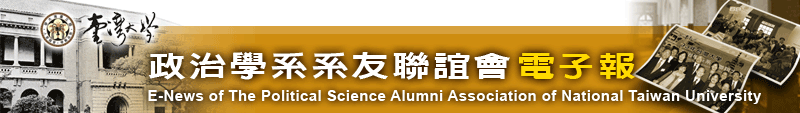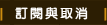2019年「胡定吾海外新銳學者方法論講座」-Julia C. Strauss教授
文、圖 柯緯倫(政治所博二)
本系於2019年續辦「胡定吾海外新銳學者講座」,邀請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與國際研究學系的Julia Strauss教授開授「政治學研究中的詮釋方法:敘事與表演」(Interpre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Narrative and Performance)」課程,並於6/18、6/20、6/22、6/25和6/27進行為期五天的演講。
講者簡介:Julia C. Strauss
Julia Strauss教授擅長結合歷史、政治與社會的大敘事,她的研究興趣包括兩岸土地改革和打造現代國家的過程、拉丁美洲、非洲國家內權力與政治表演的現象,以及中共「走出去」政策(“going out” policy)在亞洲和非洲的影響等。她曾於2002至2011年間擔任 重要國際期刊 China Quarterly 的主編,極有學術影響力。
她所出版的專書包括 Staging Politics: Power and Performance in Asia and Africa、Strong Institutions in Weak Politie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0,以及即將於今年出版的 State Formation in China and Taiwan: Bureaucracy, Campaign, and Performance。
導論: KKV之後政治學方法論之辯
政治學方法主要可區分為量化和質化研究,但Strauss指出實際上兩者都屬於實證主義的範疇之下,實證主義假設人類社會也隱含著許多法則,而研究者可以透過將主體(研究者)和客體(被研究者)、價值和事實二分,透過經驗觀察蒐集事實來驗證假說,而產生出因果機制的解釋,藉此累積關於社會和政治領域的知識,換言之,社會或政治科學的方法論實際上就是期待能複製自然科學的成功模式,知識的產出係由科學方法定義,這樣的趨勢在1994年當Gary King、Robert O. Keohane和Sidney Verba的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KKV的方法論經典之作已於2012年由群學出版中文翻譯版本,中文版書名為《好研究如何設計:用量化邏輯做質化研究》)出版後更加具有影響力,KKV的著作造成巨大影響主要係因他們大膽宣稱質化和量化研究的區分並無必要的,因為好的質化和量化研究本質上共享同一個科學推論邏輯—自然科學的因果推論邏輯,換言之,當研究設計越往統計迴歸分析的模式靠攏,則「科學性」越高,其所產出的知識的可信度和學術價值也越高。惟採詮釋學取徑的學者與實證主義最大分歧即在於,詮釋方法質疑量化和非採取實證主義假設的質化研究的邏輯是否應該一致化? 是否應該採取量化的邏輯來設計質化研究?
量化和質化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發現是否相似? 兩種基於不同假設的方法是否可以互補所短? 政治學內是否有容納多元方法論的可能呢? Strauss教授並不否認量化研究的價值,但她認為在實證主義方法之外,詮釋方法也可以對研究政治學現象做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釋,研究者應該依據研究問題而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為了符合所謂「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篩選研究的問題。Strauss的見解和Ian Shapiro(Ian Shapiro. 2002. "Problem, Methods, 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4, pp.596-619.)對於當前政治學方法論所做的反省相契合,Shapiro將當前政治學研究區分為方法/理論驅動(method-driven or theory-driven)和問題驅動(problem-driven),而目前美國政治學經驗研究大多為理論和方法前導,其結果是並未解決真實世界中政治領域眾人關心的問題,反而是曲解了資料來符合理論和方法,加深了社會對於某些政治現象的迷思和偏見。
Strauss進一步指出,在研究真實世界中複雜的政治現象,所能適用KKV的範圍是有限的,只有在特定情況下才能夠產出有效的解釋,這些情況包括合適的實證或統計資料、自變相和因變相可以清楚的獨立出來、清楚界定的問題或假設、事實和價值可以二分,惟在真實世界裡,研究者往往不容易取得現成完整的大量資料,且造成某些政治現象的自變相和因變相並不是這麼顯而易見,而價值和事實也往往是交織纏繞在一起的,而這使社會科學所處理的假設和研究問題較自然科學領域內更難切割或界定,最重要的是,即使是好的量化研究雖然往往能夠找出某種現象的模式或規律,也就是可以回答如何(what)的問題,但是卻不一定可以回答為何(why)的問題,而這正是詮釋方法(Interpretive Method)所能貢獻之處。
為什麼窮人會投票給提出讓他們更窮困政策的政黨?
Strauss教授以經典的政治學問題「為什麼窮人投票給提出讓他們更加窮困的政策的政黨」來說明詮釋方法可以如何彌補實證主義方法的不足之處。早在當川普於2016年贏得美國總統大選時,政治學界就在探討一個問題—為什麼比較貧困的郊區群眾會投給削減福利支出、減稅、倡議小政府的共和黨候選人? 有學者選擇威斯康辛州在2016年總統大選結果來分析此問題(關於2016年總統大選威斯康辛投票行為分析的文獻為 How and Where Trump Won Wisconsin in 2016,資料來源為https://www.wiscontext.org/how-and-where-trump-won-wisconsin-2016),威州在歷史上具有傾向左派的工會傳統,且自1984年以來歷屆總統大選投票皆偏好民主黨候選人,惟2016年總統大選的結果卻倒向共和黨候選人川普,根據投票的統計數據顯示,威州內比較貧困的郡與川普得票率有強烈的相關性,換言之,住在郊區、較為貧窮的民眾傾向於投票給支持小政府、替富人減稅政策的共和黨,惟實證取向的研究只能發現民眾投票行為的模式,並推論其行為背後的原因,且這種推論的背後往往是奠基於人是自利(self-interest)的假設,故在解釋威州投票行為的研究中,實證主義的的研究問題是—「比較貧窮、住在郊區的白人選民投票是否會投票給損害自身利益的政黨?」,但Strauss認為,倘若採取詮釋學視角的研究會發現真正要問的問題是:為什麼比較窮困的民眾要投票給共和黨? 他們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和自身利益? 他們如何解釋他們自己的投票行為呢? 換言之,實證主義或許可以很精準的找出人們行為的模式,能回答如何的問題(what and how),但詮釋學可以更完整的解釋政治學現象背後為何(why)的問題。
詮釋方法在研究國家的運用
Strauss指出政治學界裡不分質化和量化研究往往受到理性主義和韋伯作為典範的影響,而將研究重點放在「不存在的事物」(what is not there),將國家直接等同於一個地方的政治制度、官僚體系、法律制度,只要不存在就認為是失敗國家或還沒發展成國家的形式,並發明指標衡量民主制度和政治體系,然而,當這樣的研究典範被套用在西方以外的國家時,往往忽略了實際存在於該地區內維繫著權力運作的機制(what is there),特別是政治菁英的政治表演(political performance)和政治敘事(political narratives),當國家制度化程度較低時,統治菁英往往必須透過表演和說出群眾認同的敘事/故事,來提出政治訴求(political claims)凝聚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共識,而這種情形特別在國家歷經轉變或危機的時刻更為明顯,例如台灣民族國家認同形成的過程、甘地在對抗英國帝國主義時在所採取體制內外的政治行動,採用詮釋方法研究政治場域的表演和敘事,不只可以用來研究「為什麼」的問題,也可將量化研究以外的資料和素材(包括競選廣告、)也納入政治學研究的範疇,使研究者深化和拓展對政治現象的解釋。
詮釋方法研究政治表演的系譜學
研究政治表演的知識系譜學可以上溯到詮釋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研究十九世紀前殖民時代的巴里島的統治形態,他發現透過政治儀式和政治表演的不是要合理化政治權力的手段,而這些政治展演和文化儀式本身就是國家,他稱之為「劇場國家」,換言之,巴里島的國家統治並不仰賴有效率的官僚體系、極權統治等政治學所熟悉的型態,劇場國家強調的是透過精心安排的政治奇觀(spectacles)來維持統治秩序。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中,Charles Tilly亦都曾運用詮釋學來解釋政治現象,目前大多採用詮釋學方法的研究大多聚焦於社會運動和政治抗爭,但老師認為由上而下政治菁英如何透過表演來向做出政治訴求也是同等重要的研究課題。
政治場域中的政治表演/敘事
有三種型態的政治表演常出現在政治領域當中,第一類是國家的儀式慶典,第二類則是屬於結果半開放性的政治表演,特別常出現於選舉、街頭抗爭或法庭論辯。第三類則是微觀層次個人的政治展演。在政治事件中,這三個元素往往會同時出現,例如天安門事件中,學生跪在天安門前面,象徵的是向皇帝表示屈服,這在中共領導人和中國人的眼中的解讀是學生並非如西方媒體所報導的想要對抗政府,而是表示懇求;而之後在街頭抗爭中,可以見到各式各樣的街頭政治表演;在個人層次上,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身穿醫院睡衣與當時中共國務院總理李鵬對談,揭露了中共不願民主化的真相。
在政治場域中,政治表演/敘事出現的程度和比例會依據政治的型態而有別,當制度化程度越高,政治相關的表演的重要性和出現的機率越低;當主體可以被分割和交易時,政治表演可以發揮影響的空間就越小,例如在缺乏面對面接觸且被許多非個人化的規則所界定的市場交易中,政治表演出現的機率也較低。但即使在政治表演看似不太重要的場域,仍然可以觀察到政治表演的現象,例如稅收制度中的權力的運作可能不會表現在政治表演上,但當政治人物就稅制政策進行辯論和攻防時,仍然有出現政治表演或敘事的可能;軍隊作為一個高度制度化的組織,軍隊的功能不太可能被政治表演的影響或轉變,但在透過葬禮、軍隊遊行、慶典上,則仍可以發現國家藉著這些政治表演來公開合法化軍隊的功能和存在。
結論與討論
在短短五次詮釋方法課程中,Strauss不僅使用目前政治學界內採用詮釋學取徑的作品帶領同學進入政治敘事和政治表演的領域,更讓同學透過觀看美國影史上最重要的法庭辯論片《12 Angry Men》,了解在舉凡法庭辯論、街頭抗爭、競選等場域,政治敘述和政治表演其實隨處可見,不論是政治人物或是一般大眾都經常使用表演或敘述來進行溝通與說服,而詮釋方法是能讓研究者掌握並分析這些素材的最佳工具。最後,Struass回應同學的提問表示,採用詮釋學的方法並非否定實證主義取徑對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貢獻,而是希望同學可以思考,基於實證主義的方法和詮釋方法在基本假設上有根本的不同,是否有結合兩種不同的方法的可能呢? 是否可能達到在方法論上多元主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