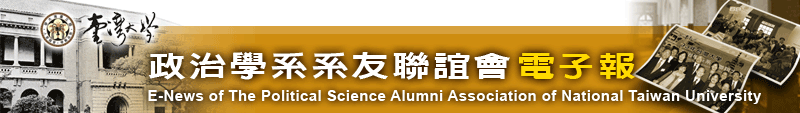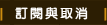2019年「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主題演講與相關活動紀要
林廣挺(碩106年班)
劉燕婷(政研二)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於2019年1月26日至27日,在臺大社科院舉辦「後西方國關理論」學術研討會,邀稿參與者包括來自本系與國內外各大學的袁易、林炫向、張登及、郭銘傑、比屋根亮太、谷巖杉等。會議並請臺大政治系特聘教授、中心主任石之瑜專題分析其近年來對後西方(post western)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本刊特邀出席該會議之該中心執行秘書林廣挺與臺大政治系碩士生劉燕婷對石教授的主講進行文字紀錄並整理節略。以下分別簡述,分享各界讀者。
一、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及方法的形成與反思
石之瑜教授首先簡介了後西方國際關係研究議程興起的過程。他提到所謂的後西方國際關係,當然是對目前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反思和抵抗,但像這樣的抵抗,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了,起於文學界的反思,尤其是對於主流的文學理論感到不滿,因此有了反思和找尋主體的行動,最早開始的是女性主義的反思,接下來是後現代思潮,一時之間解構(deconstruction)蔚為流行。
隨著80年代女性主義在國關領域討論的盛況,不但女性主義受到歡迎,當時其他的反思也在醞釀,後西方國際關係的思潮大概在1999年到2001年間興起。早在90年代初,後殖民理論便很受歡迎,諸多人等例如薩伊德、Spivak等也在那時聲名鵲起。
但在盛況空前的同時,也是女性主義走下坡和抵抗逐漸失效的開始。一方面隨著加入的人數和成員越來越多和紛雜,爭論和衝突也就不可避免,裂痕也就越來越大。當時女性主義者開始了新一波討論與反思,例如誰有資格做女性主義者?不同族裔和立場的人看法自然不同,甚至後殖民女性主義者對白人女性主義者的仇視,還大過對於主流霸權理論的仇視。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的人數已經擴張到一個飽和點(equilibrium),由於女性主義學派繼承了所有主流的規則,因此逐漸被收編和邊緣化,其作為抵抗的基地,自然不如以往。
面對這樣的窘境,想要抵抗的學者便開始思考如何重新集結,但集結所需的共同旗幟其實很難找到,最大的挑戰是2001年的911事件。這些抵抗的學者大多都不會同意恐怖主義,但他們質疑的是,用反恐的方式來因應合理嗎?他們雖然有反抗,但語言卻非常蒼白。況且因為自己的議程都依附在對方身上,所以缺乏足夠的號召力,這樣的反抗不太有效果。
為了突破困境,因此就逐漸醞釀了後西方(post - western)的概念。他們重新集結起來在Routledge出版社進行了三個系列的研究。前兩個系列的主題分別是:1.我們如何走到今天? 以及2.我們走到今天跟主流有什麼共通性與差異性。在這個過程中也碰到不少難題,例如他們要講跟主流的差異,結果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烘托出了一個主流。因此第三個系列最大的挑戰,就是如何才能超脫依附主流來理解自己的這種束縛。
第三個系列出版時,已經距規劃10年了,在這期間,後西方的議程已經逐漸成形。其核心論述是,所謂的非西方國家,無論再怎麼認真臨摹西方國家,個人如何在殖民母國的體制中力爭上游,即使後來又轉為不參與霸權和反抗,非西方國家都只能學,但學了之後發展出來的東西可能跟當初教的人想教的不一樣。簡言之,殖民母國無法完全了解殖民地,例如殖民地的人可能會有買辦心態,要拼命地學英文、法文,要模仿殖民母國模仿得唯妙唯肖,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是殖民母國,這種心態殖民母國就無法了解。殖民母國到殖民地生活,如果不想要可以自己退出,但是殖民地的人無法退出;既然有些學到的東西永遠內化不了,所以要調整,而在調整過程中因為內部的利益不一致,所以要爭鬥,這樣的爭鬥也不是殖民母國所能理解的。後西方的國際關係學者就是要整理這種心態、這種困窘(nuiansse),強調每個地方有它的特殊性、生態,這些地方到最後西方無法完全認識它,它也沒辦法透過西方來了解自己。
對此,後西方國關學者特別強調幾個論點,第一個就是差異。面對差異,後殖民學者想講清楚「我是什麼」,但後西方學者的論點卻是「我講不清楚我是什麼」。
因此,後西方的學者另一個研究的聚焦點就是,「你怎麼變成今天的你的」,這個過程中你可能沒有多想,但沒有多想,本身也是一種決定。所以每件事都是你決定好的。後西方的邏輯其實很簡單,就是被殖民主義無所不在影響的社群,如何變成今天的樣子,如何到今天的位階,而它既不是西方,也無法變成西方,更無法透過西方的理論及論述來理解自己,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你不能完全依賴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你要怎麼走,必須問你自己,你要自己負責。這就是所謂的sitedness,有site就有sitedness,其實這就牽引出倫理的元素了,也就是你必須自己為自己負責。
對此,石教授也舉自己的研究心得為例,解釋為什麼在中國的語境裡很難培養對後西方議程的敏感度。他認為畢竟在site的觀念裡,強調的是差異性,但在儒家的交往中,你怎麼作為你,我是不關心的,我關心的是自己怎麼跟你相處,而不是你是怎麼樣的人。儒家文化中認為過度好奇是很怪的,甚至認為朋友是很糟糕的關係,君子之交應該淡如水,不應該太好;朋友關係是圍繞其他四倫發展的,而不能過於親密,影響其他四倫的發展。所以諸如curious、sitedness等特質和概念,在儒家文化中不容易培養,但後西方研究的關鍵就是要很curious的去整理這些東西,以了解彼此的差異是什麼。中國的儒家文化就不鼓勵這種curiosity,中國在意的是自己要如何跟各國交往,而後西方的研究則是想要找出世界各地有哪一些地方跟西方不一樣,然後把他們全部找出來後要去保護它。以上述的內容為背景,石老師也提出兩點對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反省和修正:
1.中國比較感興趣的是所謂的非西方的國際關係(non-western IR),這個學派到每一個社會去找被西方影響之前的傳統,看看這些傳統能不能變成我們能理解的資源,然後才會有所謂的Global IR。而以系譜學為內涵、強調sitedness的後西方學派則認為既然已經被改變了,就不可能回頭。後西方的主張具有很強的線性史觀,既然往前走了,就不要再往後看了。但石老師認為,其實那些被消滅的機制,還是有可能會在未來又冒出來,所以未必是線性的,也可以是循環的。
2.後西方拼命去找各地跟西方的不同,他們的用意在於強調:「沒有西方了,因為大家都是後西方!」,但在實踐上,反而鞏固了一種本體論上的西方。石老師於是提倡把所有西方國家當成後西方來研究,雖然現在還看不到。例如紐約、加州,如果把他們當成後西方來研究,這完全是可以的;但現行的做法卻都把它們當成cosmopolitan來研究,然後把其他的理論都邊緣化。所以石老師認為,如果要做後西方研究,就必須要平等,把所有國家都當成後西方。就像東方主義,也不是鐵板一塊,應該也要把整個東方主義當成後西方來研究,找出各個差異。
二、對文明衝突的後西方回應-The Clash of Relations and Its Mechanisms
石教授以前述內容為基礎進行延伸,針對所謂文明衝突的議題,提供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視角的回應。首先,石教授對於後殖民國際關係中常講的hybridity提出了一些解釋和反省。因為,雖然曾經被殖民或是刻意的學習,非西方國家既無法將自己的文化改造的和西方一樣,但卻也無法完全拋棄過去,因而呈現出一種混血(hybridity)的「尷尬」狀態。相較於去殖民和全盤西化這兩種極端的反應,後殖民學派則強調既要反純淨、但又要反霸權,要承認和重視本身的hybridity特色,而不是去消滅它。
全球化時代幾乎每個國家或個人都是hybridity,這似乎是很正常而且具有正面意義的事。直到911事件,讓人體悟到hybridity潛在的破壞力後,hybridity的特殊意義和研究的價值才又顯現出來。那是因為,911事件本身就是一種全球化下hybrid的現象,但美國卻抨擊他們是fundamentalist,所以美國霸權搖身一變成了hybrid的代表,明明是hybrid的恐攻團體反而變成了fundamentalist。
石教授因而提出所謂後混血(post-hybrid)的概念,強調hybrid在實踐上並不是那麼浪漫的事。Hybrid也重視site,但它的site是實體(physical)的。在全球化時代,每個地方和人都需要被代表,大家都要自己找到某個元素來代表。那麼如果在同一個site上,我們都是hybridity,那麼誰可以出來代表我們,這又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
對於在這種情形下,後西方學者該怎麼研究hybridity,延續前一天上午石教授對後西方理論的反思,他認為這就要用到循環(cycle)的觀念,也就是本來被消音了50年、甚至是100年的聲音,為何又被叫了出來,例如日本首相安倍就帶有某種祖父輩的懷舊情懷。如果被打散的力量又能再集結,這就可以提醒我們:如果抓到了正確的催化機制(trigger),就能把一些看似分散的力量集結起來,成為一股壓制性的力量。
因而石教授認為,即便在post-hybridity的時代,文明衝突的問題仍然有可能。在國際關係學界反駁文明衝突論最不遺餘力的學者Peter Katzenstein認為文明交流一定是雙向的,不是單向的,例如sinicization一定是雙向,因為其中包含中國去學別人,還有別人來學中國。但他要抵抗文明衝突論最大的挑戰,就是他如何定義「文明」。直到今日,他還沒找到一個篤定的定義。
石教授比較偏向把文明定義為:Anything the one believe we can learn,這樣就把civilization當成一種judgement,就是如果我覺得這是我可以學的,這就是文明,如果是我學不起來的,就是文化,civilizational-orientation心態就是:我覺得洋人的東西是我可以學的,我的也是洋人可以學的;cultural-的心態就是:我覺得洋人的東西是我學不起來的,我的洋人也學不起來。當然實際上學不學得起來又是另一回事,而且這種心態會隨practice而改變,所以可能今天覺得可以學,明天覺得不行,如果我們把civilization與culture當成judgement了,那麼有兩個好處:我們因此能分析行為者的心態;我們容許行為者做改變。
回到目前國際關係的實踐,石教授觀察到近來中美關係,出現了許多話語。美國有些人把中國想像成明朝,把中國當成一種無法向美國學習的政治體。在戰前日本的世界觀中,只有它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因為西方人不懂東洋,東洋人不懂西方,所以他想像中的二戰是個文明戰爭,就是要集結東方的力量打那些西方人,然後用自己學到的西方現代性教訓這些不知長進的東洋人;結果日本人想錯了,二戰其實是西方跟東方一起打另一陣營的東方西方,所以訴諸文明衝突沒有動員成功;展現現代化力量的策略也沒有成功。
日本誤判了文明的力量,以為共同文明會集結在一起打文明戰爭,所以失敗了。當然也是有成功的案例,例如英阿福克蘭戰爭,美國就站在英國這邊。石教授認為,雷根所做的選擇並非是國家理性必然,而是透過judgement,社會科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去證明行為者做決策的原因可能是結構性的,也可能不是結構性的,也就是judgemental的。古巴飛彈危機時,甘迺迪也未必一定會封鎖古巴,決定都是剎那間的事。所以國家戰爭時要站在哪一邊,就跟人一樣,都具有多重關係( multiple relations),要看誰如何召喚和動員。
石教授認為,文明會被視為衝突因素,是被trigger出來的,所謂trigger就是政治正確,也就是要動員。動員有分層次和程度,送禮是小動員,講國家民族的大道理就是大動員。所以,其實所謂的文明衝突,並不太容易被trigger,但也不能說就不存在,它其實是程度問題,而不是絕對問題。你永遠能透過對於文明的trigger,讓大家產生evaluation,也就是先在情感上讓你極端恐懼、厭惡,這樣就能影響大家的行為。文明衝突可以發生在兩個人之間,而且更容易,造成的結果比較不嚴重。但是如果是團體間,結果就會比較嚴重。例如如果在印尼社會宣傳儒教,就會有比較大的危險。
因此,如果要認識hybrid的危險性,就要把post-hybrid的概念拉進來,讓hybrid的危險性被看到,也就是不同的元素雖然暫時混在一起,但其實一旦受到政治正確的動員召喚,就有可能會輪流出現,歷史其實是循環的。一旦被叫出來,人就要被迫選邊,因此讓衝突的機率上升。文明衝突並不是兩個固定存在的文明在對抗,但是透過practice,可以把一種文明關係變成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性質的論述,就能夠找尋對象進行動員,接著對方就被civilizational relations給constitute了,進行以文明為名義的衝突。而如果有一方要你學他的東西,但你又不想學時,才比較容易出現文明衝突,而一國國內政治上的選邊,會影響到另一國的選擇。我們要研究的是,文明衝突的話語會如何對我們產生影響,那麼我們就能知道,政治正確動員我們的機制是什麼。
三、總結
石教授主題演講之內容是以其過去多年從事國際關係和中國大陸研究的累積作為基礎,並聚焦在近五年裡他對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初步研究成果。其研究成果和目的主要包括梳理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議程之所以能夠形成的脈絡,反思其盲點,並指出未來可行的修正方向;再就是針對當前國際關係似乎重現的文明衝突議題和爭論,以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視角,提出深刻的見解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石教授講述完成後,與會師生也積極提供反饋意見,並在後續議程中分別討論研究成果,會議在27日下午圓滿完成。

母系系友與各校與會學者參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