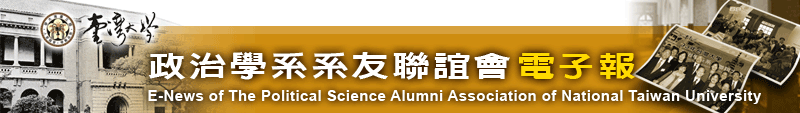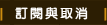專訪本系系友:蔡政文名譽教授
林宜汶(政研三)採訪整理
 蔡政文名譽教授
蔡政文名譽教授蔡政文老師畢業於成功中學國中部與省立板中,於1958年考取本系。家人原希望蔡老師習醫或其他自然科學,但蔡老師早歲即對政治事務深感熱情,本系成為優先志願之一;當年正好學校打破學系分組,蔡老師考取不分組的政治學系。在學期間,受到比國旅台天主教神父鼓勵,於1963年赴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博士,見證了戴高樂時期與1960年代動盪的歐洲。蔡老師在連戰教授擔任母系主任時返校任教,多年來執教母系「國際政治理論」的相關課程,許多現在我們所熟知的政治系三組優秀師長,都曾受教於蔡老師門下,後來也在他主持系務時返校任教。而蔡老師不只擔任過本系系主任,更曾為當時政府的核心幕僚,應用所學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無論在學界或是政界,都有極為精彩的人生閱歷。108 年是蔡老師八十歲大壽,本系辦理了研討會共同歡慶;本刊特地邀請蔡老師與讀者分享學思歷程,並勉勵後進系友與師生。
問:請問老師當時為什麼會選擇就讀政治學系呢?
答:考大學時,父母其實希望我就讀醫科,因此,當我將第三志願填臺大政治系時,母親小有反對。我當時告訴她,如果我沒有考上醫科,讀文科的政治系會讓我有比較多時間準備重考或轉系考,母親才答應。但事實上政治系才是我自己的心之所向。我對政治感興趣,其實也是源自於父親的啟蒙。從小我就經常聽父親講論政治,因此對於投身政治工作有憧憬。而選擇政治系,也是因為我希望未來有機會投身外交工作。最後更是因為父親的支持。我還記得當年大專聯考採不分組考試,作文規定毛筆作答,這在前後屆都沒有。考上後,儘管班上有一半的同學大一結束都轉系,父親說服我的母親讓我繼續留在政治學系追求我的理想。我在政治學系確實念出興趣,大學四年也幾乎年年都拿書卷獎,最後更名列前茅畢業。
問:一直以來,本系大多數老師海外留學時都會選擇美國,但老師您卻是去歐洲,而且是在比利時的魯汶大學讀博士班,想請問老師當時的抉擇歷程,並分享求學經歷?
答:早年我想過三條人生規劃:外交官、國際組織任職,學者。選擇歐洲,是因為我原先希望如果留學後歸國,有助從事外交工作。我認為英語組的競爭太激烈了,若能到法國留學,學法語,考取歐洲語言組也許更有所為。然而,當年在畢業之後,我還要再當一年兵,因此無法直接考法國政府的留學獎學金。因緣際會下我認識的一位比利時神父知道我有意赴歐洲留學,便推薦我比利時的魯汶大學,我順利申請到學校後,魯汶大學也願意等我當完兵再過去就讀,因此最後便選擇到比利時留學,並一直得到該校獎學金至畢業那年。
這段留學的日子,對我有不少深遠的影響,首先就是影響我的職涯選擇。我原先想當外交官,但在歐洲留學的日子,剛好有機會到當地的中華民國大使館打工,記得當時館長是陳雄飛大使。後來我發現在外館工作,有很多需要送往迎來、交際還有安排庶務的任務。我自認不是這麼善於應對,也不是很喜歡反覆熟練的庶務行政,因此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另一個加深我這個想法的原因,則是十年的留學生涯,在海外孤身一人的經驗,讓我決定以後不要再長時間駐留在海外工作。
我在歐洲讀書的期間,剛好是1960年代,世界局勢與歐洲政治風起雲湧的時刻。有趣的是,我還在歐洲時,當時中華民國與比利時和法國都尚未斷交,因此我見證了中華民國的外交挫敗進程。時任法國總統的戴高樂,也在政治界掀起一波風潮。我非常欣賞戴高樂,認為他是法國最後一位帶有浪漫與人道主義情懷的政治家。他敢作敢為,企圖在美蘇兩極體系的格局下,讓法國走出不受制於結構的第三勢力路線。儘管最後並非成功,但他的理念與作法依然深植人心。而戴高樂當時的一些見解,從事後諸葛的角度來看,也確有其道理。例如他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從今日的脫歐風波,可見其高瞻遠矚。畢竟英國長期以來作為歐陸國家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不強調「歐化」,戴高樂就說它實在是一個「大西洋國家」,著實跟歐洲政局格格不入。
問:請問老師認為歐洲與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科訓練與研究視野有哪些差異?
答:我認為美國講求「專才教育」,而歐洲講求「通才教育」。在歐洲求學時,我們有大量的課程要求學生在道德哲學、形而上、社會學、國際關係史等方面扎根,希望學生掌握深層的知識脈絡後,再來分析問題。我記得當年在比利時僅僅政治思想必修,就佔了兩年共20學分,我自己的指導教授也是教國際關係史的。這點也反映在國際政治場域上,美國講求大戰略(grand strategy),國家利益至上的現實主義途徑,但歐洲卻經常更強調宏觀、深層的歷史背景分析,以及追求理想與價值的色彩。當然,美國流行建構主義後,歐洲也很受建構派影響。我認為比如雷蒙.阿宏(Raymond Aron)的國際政治研究視角就強調要有對社會總體的認識,要有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知識基礎。美國主流途徑是一開始就強調「專化」。「行為科學」派認為歐洲途徑似乎不夠「科學」,現在更走上「數字化」,但欠缺總體認識下的數字,是不能解釋事實的。
無論如何,我認為美歐兩途徑並非互斥,甚至應該要能兼容。所以我返回臺大政治系任教後,要求國關組的學生必修政治思想史與比政,就是希望學生除了傳統政治學的途徑外,也可以從歷史、哲學思想與比較的角度,更加了解這些議題對社會變遷的影響。除了前述的歷史、社會學與哲學途徑,文學與文學批評也是歐洲社科常整合的對象。我在歐洲讀書時就曾和就讀文學的同學一起研究過,發現戲劇批判中,也隱含政治學關心的議題,像是階級,甚至是自由市場批判等。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學習如何將理論與思想應用在現實中來進行分析。
問:儘管老師最後沒有投身外交工作,但在研究講學之餘,也曾有機會在政府單位擔任重要職務,想請問老師認為學術工作與政治工作有何異同,如何相輔相成?
答:我認為從政經常需要做決策,而且主政者做決策,往往也會受制於人的因素,像是選舉等。但學者的工作,則是要細細研究問題,提出全盤、周延的考量,未必急著提出單一的解答。因此,到了政界,我也是選擇做決策諮詢(brain trust)的工作,讓我能專心做自己擅長的研究分析,再提案給主政者參考,讓他們自己來做決策。這種角色與我的性格較為相符,也是我認為較能貢獻所長的方式。
五、現今全球有一股民粹主義的潮流,老師如何看待這股風潮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答:我對此抱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在我看來,人類社會總有兩大週期在循環:「累積週期」與「摧毀週期」。在累積週期,人類致力於生產、增加人口與財富,一直到飽和狀態,人口過多、資源消耗過多時,就走入摧毀週期。摧毀週期來臨時,戰爭、天災、瘟疫帶來危機,摧毀了許多前面累積的資產。民粹主義正是這個摧毀週期的一種表現。所以民粹主義並非空穴來風,它是因為我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已經遇到某些無法解決的問題,出現危機,這時人類就自然而然會傾向期待「超人」橫空出世,才興起不少能夠鼓動民心的魅力型領袖。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風潮並不會持久,因為民粹超人只有在選舉時有煽動力,選舉結束後,依然要回歸正常的政策與治理。如果真的端不出政策牛肉、無法解決問題,每次都靠民粹動員,民心也會疲乏,不可持久。因此,有穩健的制度、有持續推動政策的人,對於抵禦民粹帶來的摧毀效果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也不必太過於悲觀。我認為像是歐洲興起的極右派,社會支持最多就是百分之廿多,《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所說的條件,資訊時代仍然存在,民粹危機還是不容易走向戰爭。
問:老師對於系友、年輕後進的期許?
答:首先,要有健康的身體跟穩定的精神,這是我們去追尋一切目標的根基。我的職涯道路上,有不少大有可為的同事,就是因為身體健康的因素,而影響了他們的發展,非常可惜。第二、語言能力很重要,能有第二外語更好。因為語言就開啟了我們接觸更多不同視角資訊的能力,可以拓展我們的視野。第三,誠如前述討論歐洲問學的途徑,講求跨領域整合,我也鼓勵大家除了政治學本科,多涉獵各種不同領域的知識,幫助我們以不同的理論視角和研究素材,開拓政治學的疆界。第四,多結交朋友。人生需要不講求利益的朋友,彼此勉勵、進步。特別是到了年長時,要有一兩位知心朋友,穩定心情、相互支持。第五,善待家人,家人真的是一生中陪伴我們最長時間的一群人,因此我們一定要好好珍惜與家人之間的緣分。
 蔡政文老師參加 2010 年外交部系友餐會
蔡政文老師參加 2010 年外交部系友餐會
 蔡政文老師於 2010 年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蔡政文老師於 2010 年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蔡政文老師出席本系主辦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蔡政文老師出席本系主辦國際關係理論學術研討會
 蔡老師 80 大壽餐會合影
蔡老師 80 大壽餐會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