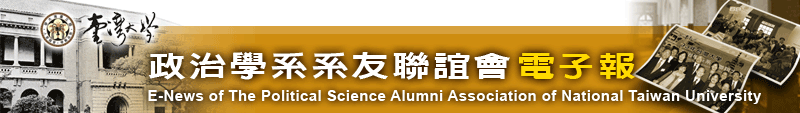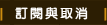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追思許介鱗老師(50年班)
張鈞凱(93年班,碩101年班)
 時任法學院院長許介鱗教授與夫人傅琪貽教授(前排右),於許院長以「亞洲文藝復興」構想整修徐州路校區動工前,在校門口設祭祈求平安。(傅琪貽教授提供)
時任法學院院長許介鱗教授與夫人傅琪貽教授(前排右),於許院長以「亞洲文藝復興」構想整修徐州路校區動工前,在校門口設祭祈求平安。(傅琪貽教授提供)
許介鱗老師在7月1日晚間10時10分過世,那一夜收到傅琪貽老師的訊息,久久無法入睡。因悲傷而來的思緒紊亂,不知不覺思忖著老師選在這個時間遠行,是不是有他的遺意?7月1日,香港回歸;10時10分,雙十紀念。帝國主義的批判,孫文行誼的研究,一直是老師學術研究關注的重點。
疫情之前有一次去探望老師,他送了我一份文章〈追思小林直樹老師及求學記〉,這是許老師在東大求學時期的「回憶錄」。他用漢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很難活過百歲,而常憂慮千年後之事)的精神與情懷,來形容其業師小林直樹教授,以及其終生維護和平憲法理念對他的影響。文章同時回顧了老師如何以批判丸山真男的「近代化」,從而萌發其博士論文選題,甚至延續至畢生的思索與信念。「讀了這篇文章,你就會明白我的思想」,許老師用著微弱卻堅定的聲音告訴我。
在我這一屆及其後的系友,對系上有一位許介鱗教授,恐怕已不太熟悉。當時許老師在大學部並未開課,研究所則有三門選修課,我在研一時分別修了「臺灣政治史專題」與「臺灣政治發展專題」兩門課。在政治學量化研究大行其道之際,做為一名「學徒」,卻格外喜歡這兩門講歷史、談思想的課程。許老師爽朗的笑聲,自信又霸氣的語調,以及天馬行空的論點,至今都令我印象深刻。
許老師是我對徐州路校區情有獨鍾的理由之一。行政大樓門內掛著奔放手寫的「亞洲文藝復興」匾額,校區外牆柱上鑲嵌著不同的陶瓷版畫,都出自許老師任法學院院長時期之手。猶記每次上課之前,我都會先跑到許老師在法律系大樓的研究室,向他請教被政治迷霧所湮沒的臺灣史,或者聽他縱議時事,都是我的思想養成期的重要養分來源。當然,對於許老師那一間透著些許陽光、擺滿書籍,還放著一副孫文畫像,卻沒有電腦、印表機等電子設備的研究室,到現在彷彿還能聞到裡面那股特殊迷人的味道。
 碩士畢業與許老師合照
碩士畢業與許老師合照
一次在課堂上,許老師有感而發,說道政治學研究靠得是「想像」(imagination)。同學們懵懵懂懂,我也不例外。後來在老師的指引下發想報告題目,陸續寫出「陳水扁與李遠哲」、「馬英九與保釣運動」,得到老師的好評,後者還出版成書,由許老師賜序。還跟著老師讀了「中美網路戰」,Joseph Stiglitz的《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以及他當時新出版的《日本崛起的奧秘》兩冊。再經過多年咀嚼,似乎慢慢理解了老師所謂的「想像」,或許正是來自於對於世間萬物充滿好奇,對於世界大小變化充滿敏銳,也對於強權與弱小分別充滿了反省和憐憫。
許老師為拙作惠賜的序文開頭寫道:「作者張君1985年生於臺灣雲林,我是1935年生於臺灣新竹市。我們年齡相差50歲,有半個世紀之多。在課堂上,我們切磋琢磨,我的生命還有一點點火焰燃燒,都是靠這些年輕人提供燃料的能源,傳遞不熄的煙火,而不知不覺地燃燒起來。」他年長我祖母一歲,一位是我在學校最敬仰的師長,一位是我在家裡最敬愛的長輩。厚顏的說,我對許老師的感念,除了「師生緣」之外,多少還帶著一點「祖孫情」。
許老師的《日本殖民統治讚美論總批判》、《臺獨脈絡記》等遺著,是我時不時翻閱的作品。回首校園時期與出社會之後,許老師帶給我的思想啟發和教誨,在我心目中,他也是「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當之無愧的先驅者。
 2017年4月17日在「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拜訪許老師
2017年4月17日在「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拜訪許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