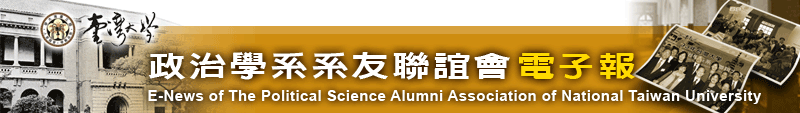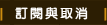緬懷母系朱雲漢教授(66年班)
吳玉山(69年班)

懷念雲漢
雲漢走了,好像天邊璀璨雲彩翩然而去。我覺得此時他想看到的不是大家的驚愕、悲歎與不捨,而是記得他一生的成就與風華。簡單地來說,雲漢是世界級的政治學者,溫柔敦厚的儒士,滿懷家國情懷的知識份子,以及善於品味人生的大師。這四點,缺一不足以描摹雲漢。
雲漢是臺大政治系大我三屆的學長,在學校就有才子的名聲。1987年他從明尼蘇達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回母系任教,我四年後繼之,從此我們在政治系做了32年的同事。後來胡佛院士倡議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政治學研究所,先成立籌備處,我們二人乃一起去中研院,為新所打基礎,但仍在臺大合聘教書。當時由我擔任籌備處主任,雲漢是所裡敦請的第一位特聘研究員。中研院的這一段,我們又同事了21年。這兩份同事的情誼,如果加起來超過了半世紀,相處時間之長,應該是少有的。
雲漢是世界級的政治學者,毫不為過。他師從胡佛院士,是胡老師的大弟子,從臺大組建第一個調查研究團隊時,就參與其中。胡老師的這個計畫,後來擴展到兩岸三地,而且在雲漢回國後,逐步擴展成為亞洲民主動態調查(ABS),並與世界民主動態調查連繫起來,組成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網絡。這是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下從民主價值變遷的角度來進行的一個規模龐大的國際政治學研究計畫,而雲漢承接著胡老師,帶領臺灣的學者,在這其中取得了亞洲地區的領導性角色。如此成就在全球華人政治學者當中是空前的。雲漢與亞洲及全球從事民主化相關調研的學者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建立起聯繫網絡,相互支援,並且獲得了國內與國際許多主要研究基金的支持。其規模在臺灣的政治學界無疑是最大、也最為持久。
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政治學術組織的建構,是極為艱辛的。ABS除了直接進行一波波的調查研究之外,又指導與支援了多個國家的調研工作,並整合建立了整個區域的資料庫,扮演行政協調的角色。其中各式各樣的討論談判、折衝尊俎,極為勞心費力;而為計畫持續籌募研究資金,更是雲漢直到過世那一天都時時刻刻、心心念念的大事,這對他的病情無容置疑地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雲漢是一位溫柔敦厚的儒士,這一點跟胡佛老師一樣。他們一心嚮慕西學,如五四諸子一樣想用民主與科學來救國,但是其待人處事完全是溫厚的儒家典型。雲漢對學術前輩執禮甚恭,對同儕慷慨大度,對學生則關心照顧、非常溫柔,和他相處過的人絕不可能無感。他才思敏捷但絕不盛氣凌人,執著理念但溫和婉轉,不在同一個文化情境之下的外國學者也樂於和雲漢合作相處。記得一位很資深的美國政治學者前一段時間來臺,但是沒有見到雲漢,深感可惜,他在臨行前跟我說“Yun-han is such a sweet person”。我想了一下,瞭解到他這樣說的原因,是雲漢總是熱忱地接待國際學者,並且體貼地為他們的研究需求多方設想。我和雲漢有一些共同的學生,即使在國外教書發展還是持續保持聯絡。這些學生回臺灣來的時候一定會來看老師,而我也因此知道雲漢對學生的關照是如何體貼入微。不論是以前還是現在的學生,能被大師鼓勵肯定,是會長久記憶、甚至影響一輩子的。雲漢這樣感動了好多的學生,讓他們走上了學術的志業。
雲漢的儒士之風還可以從另外一角度來看。多年來我從旁觀察,深深感覺到雲漢對胡老師不僅是當成恩師來尊敬,而胡老師對雲漢也不只是當成他的大弟子來培養提攜,他們兩人是情同父子的。胡老師在引進政治學的科學方法以及開啟調查研究的風氣潮流方面是國內第一人,而雲漢則完全繼承了胡老師的理念。在2018年胡老師過世,雲漢為胡老師盡心籌辦了一場追思會,並在會上為臺大社科院的「胡佛東亞民主中心」揭牌,場面非常感人。這當然是為了紀念胡老師開創的功績,也是充滿了雲漢與一整代學術界對胡老師的師慕之情。從這些師生的互動,我看到儒家的風範,也看到中華文化傳統中美好的一面。
雲漢是滿懷家國情懷的知識份子。雖然他的研究多是運用數量工具來進行精細的社會科學分析,但是他的起始點與一貫的初心是高度理想主義的。以前胡老師在教導臺大一屆屆學生的時候,總不斷提醒大家要盡一個知識份子的責任,講到「知識份子」這四個字的時候,語調一定特別高昂。我知道那是一項期許、一份使命感,和一種甘盡全力、願意為理念而犧牲的心態表述,展現的是對統治者的一種寧折不彎的骨氣。在這種心情之下,雲漢始則以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為圭臬,並研究在臺灣如何進行民主轉型,又如何可以達成民主鞏固,這反映在他前期的專書著作,包括Crafting Democracy in Taiwan與《臺灣民主轉型的經驗與啟示》當中。到了後期,雲漢觀察到民主體制在實際運作上的種切缺失,乃又不惜與多數意見相抗,坦率地批評西方民主,並指出中國與東方的興起,以及中國模式有其合理性,而後者在臺灣是有極大的政治爭議性的。他的《高思在雲》、《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與和鄭永年主編的《西方中心世界的式微與全球新秩序的興起》是這個階段的標誌型著作。雲漢最後一篇公共論述,是在過世前一個月在《天下雜誌》發表的「美國軍售地雷,臺灣必須覺醒」,縱身躍入一個爆炸性的議題當中。雲漢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憂國憂時,發抒己見,無論在什麼樣的政治環境,都慷慨陳辭,這份志氣,也是從恩師胡院士那裡一脈相承下來的。不同意雲漢觀點的人,可以和他進行學術辯論,但是不能夠否認他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和油然而發的諤諤之言。
最後,雲漢是善於品味人生的大師。許多與雲漢相識的學術中人,都知道雲漢對生活有藝術性的品味。他是一位美食家,對於東西菜餚、名家餐館如數家珍。他在國際行走,又在對岸走遍大江南北,閱歷豐富,無論品茗、論酒,指點佳餚,勝過專家。去過蔣經國基金會、受過雲漢招待的學者,不可能不驚訝於主人的精緻品味。我最嘆服的,是雲漢以逾十年的努力,百折不回地建構了七海文化園區,創建了蔣經國總統圖書館,其建築的巧妙佈局、色調的層層搭配、雅致的多樣選材、與氣魄的開闊展示,都讓人讚歎不已。在宴會大廳旁的牆上,有一幅胡老師所寫的蘇軾「念奴嬌」,從大江東去寫到一尊還酹江月,氣勢磅礡,筆力萬鈞。這也是雲漢最愛與人介紹的,一來展現出胡院士的名家書法,一來也更讓人感受到雲漢對恩師的敬重與推崇。
一位碩學鴻儒、謙謙君子、憂國學者、品味大師從此仙逝,但是他所遺留的,何其豐富。如何讓他所夙夜經營的能夠長久存留,持續發揮影響,而不至人走茶涼,會是懷念雲漢的人所該心心念念、不能遺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