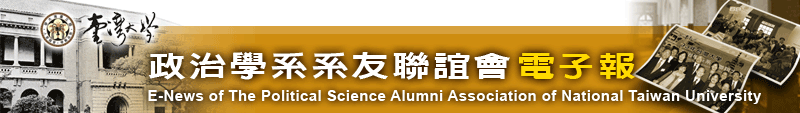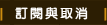新進教師專訪 ——— 李仲軒助理教授
採訪整理/田文彥(政研一)、彭詠晨(政研一)
圖/郭銘傑副教授

一、想請問李老師的求學經歷,是否有特殊的因素激發老師對於學術研究的熱忱?您對想要攻讀博班的學生有何建議?
其實關於對學術研究產生熱忱的契機,有的時候沒有想像中的戲劇性,比較像是對自己、對社會、對學術工作長期累積的觀察所共同造就的。
從大學時期我就屬於比較會對知識感到「好奇」的學生,除了「實用」的法律知識外,還很喜歡聽一些似懂非懂的東西,心理、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相關的課程、演講與社團也都會去接觸,而且當時法律學院還在徐州路校區,包含法律、政治、經濟等科系都共聚一堂,使得跨域學習相當方便,例如當我決定投入公法的研究,就很容易更有系統地選修政治系相關的課程。
雖然我蠻喜歡嘗試跨越自己既有知識體系的邊界,但跨界不一定會成功。回首過往很多時候會發現,許多嘗試的最後還是沒有辦法和自己的知識體系產生有意義的連結,反而變成零碎的,破碎的東西。沒有得到預期成果,當然不無遺憾,但我覺得不必太在意。知識體系的塑造,沒法太講究效率。如果抱持單純的好奇心,以不那麼功利的心態,隨性隨緣地栽培自己知識的花園,又能自得其趣,那麼你可能就相當適合學術研究的工作。岔開來說,在學習的過程中,尤其是越早期階段,盡可能把觸角打開,知識體系的地基打得越寬廣,其實對未來學識開展會有很大的助益。
其次,現在就讀大學,雖然現實層面上,當然主要還是職業與就業上的考量,可是如果計畫要繼續去攻讀研究所、博士班,甚至要獻身學術界的話,恐怕就必須要更清楚地認識到,源於西方、現代意義的大學,其本旨是給對於知識探求、對於認識真實有熱情的人提供理想的環境。
正因如此,若真的要講契機,我覺得是自己對自己的認識與省思。而這個反省其實應該是越早越好,在大學時期,最晚研究所時,就應該問自己,「進大學到底為什麼?」、「進研究所到底為什麼?」我希望同學們可以更早就開始思考Advanced Study的目的究竟為何?尤其如果要真的想要進入學術這個圈子,甚至是變成是一份職業,或者志業的話,一定要對自己與學術研究有很清楚的省察。
因為事實上大學是社會中一個很獨特的機構,大家都講大學自治,但大學為何可以自治,或為何需要自治?不是因為大學成員高人一等,而是因為大學和其他的社會機構很不一樣,其獨特性在於,大學,可能是社會上唯一可以容許、甚至鼓勵這麼恣意地追求真實的機構。大學的精神就是追求盡最大可能如實照見這個複雜的世界。除了從事學術研究的教授及研究人員之外,在大學裡面的學生受到的訓練本質上也是要「求真」。
然而就「社會事」而言,求真可能是件很無謂的事,是把簡單的事弄複雜。大學的課程或訓練不見得對社會很實用,甚至常常被講說「這很蛋頭」、或「知道這個要幹嘛?能賺錢嗎?」甚至努力證明出來的「事實」,可能只是一些大家本來就「知道」的「常識」。
進一步說,是不是讓所有社會的成員,都以大學所教育的方式思考、行動、進行,對社會運作最好?其實也不無疑問。如果把大學所使用這種思考方式無條件地移植到社會或團體生活去,其結果可能會亂成一團。當每一個人都互相用學術思辨的方式爭辯,以發現真相為依歸來處理各種事務,不見得是對社會運作之效率有幫助。至少以個人層次來說,素樸簡單的信念也許可以讓日常生活過得更好。
總而言之,求真是一種很奢侈的事,不是每個社會、每個人都能承擔這麼奢侈的活動,甚至可能只適合存在於社會中一個特定的環境裡面,這就是大學的特色、就是大學的目的。為了實現追求真實的目標,在大學裡面必須可以完全自由地作各種特異的思考,發表各種有時候很討人厭的獨特言論,而社會全體不但要供養,還要包容這樣一個機構,並讓大學能夠自治以維護了這樣一個非常獨特的自由環境,大學也因此應當對社會負有相當之責任。大學或許本就不求準確回應社會的每個務實的需求,但還是要有一種追求無用之用的理念與責任。

二、接著想請問老師是否能和我們分享為什麼想赴英求學,以及留學的心路歷程?
這個其實是延續上面對於學術研究的討論,只是還需要進一步思考,一個現在越來越明顯的現象,台灣現在的線上資源這麼發達和普及,已經不是三,四十年前是國外才有教育資源而台灣沒有,所以必須赴西天取經。如果同樣讀這些書,上這些課,在台北跟在倫敦有什麼區別?
正好前兩天在看訪綱的時候,我想到有一段話可以為這題作很好的詮釋。其實就是〈蘭亭集序〉這幾句,「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這幾句話很好地詮釋了我當時的感受。
對我來說,雖然仍遠遠不足,但赴英求學讓我有機會拓展、型塑自己的世界觀。真實世界的複雜與多樣,遠遠超出我們所能想像,必須切切實實見識到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異士奇人,更是所在多有。
在不同的自然、物質環境下,不同的歷史、文化、宗教,造就不同的國家、種族,加以不同的地域地緣、不同的飲食、不同的(多元)性別、不同的階級、不同的學術訓練系統等等,所形成的理論觀點與學術研究可能大異其趣。這種經驗對我來說是相當震撼的。很多我們認為事關重大或理所當然的問題或理論,在其他人群來看可能無足輕重,也未必能拳拳服膺,當然反之亦然。
對我來說,拓展自己的世界觀,不只是願意收看國際新聞的「國際觀」,更是對複雜世界中真實存在的,不同的認知、不同的定義、不同的擔憂、不同的關切、不同的喜悅、不同的憤怒、不同的悲傷,都至少願意努力去理解、尊重,甚至共情。舉例來說,關於近期歐美多所大學爆發學運的事件,對臺灣的大學生而言,我們當然很容易能透過新聞媒體獲取即時資訊,但對於他們爭取的訴求,若非真正設身處地,即便同為大學生,卻可能永遠難以理解,更未必能產生廣泛共鳴。因為我們需要更深刻的相互理解和體會才能賦予這些資訊意義。
這種世界觀的養成,未必是出於課堂上的講授,反而仰賴日常中點點滴滴的薰陶。在倫敦,你不需要額外取一個去脈絡的英文名字,而是直接用自己原本的名字拼音。周遭的朋友、同學、同事等,即便需要反覆確認、學習正確的發音,都會堅持要用你真正的名字相稱,不會因為便利,期待你變成他們熟悉的Harris或Joanne。從尊重開始,漸漸的學習共情,感受其他人的喜怒哀樂,欣賞別人的觀點、理論、研究。當我們確實真正認識宇宙之大,懂得欣賞品類之盛,不必經過刻意教導,自然懂得不足謙遜,自然懂得需要精進學習。
再來還有一件有趣的事,如果不瞭解英國的大學生態,我覺得可以去看哈利波特。倫敦大學就像霍格華茲一樣,有多個獨立運作的學院各自教學。雖然有一定的聯繫,但學術風格和取向上各異其趣,甚至各行其是。但就如這段話所說,「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因為各自的種種差異,產生分歧的視角和觀點,使強有力的論辯得以相互激盪、欣賞。這樣的環境在學術和知識上讓人興奮,身處其中真的會讓人覺得「不知老之將至」。
Samuel Johnson博士曾這麼說,「如果你厭倦了倫敦,你就厭倦了人生」。所以我有時就想,儘管倫敦的生活如此精彩,但在厭倦倫敦之前,要趕緊回到台灣,否則真厭倦了人生就不妙了!
三、仲軒老師您研究跟環境相關的議題,是出國前就決定了嗎?還是說到了英國之後,才投身這個領域?
其實都有。這裡可以先提一下,由於英國博士學制屬於師徒制,在出國前一定要先提交研究計畫給可能的指導教授,唯有引起其注意以及指導的興趣,才有入學之可能。然而到了英國後的第一年,也就是所謂MPhil階段,其實是非常崩潰的過程。在那一年中,我絞盡腦汁,寫了至少四、五個版本的研究計畫,但是一直被我的指導教授退回,要求重寫。一開始我感到非常困惑,之前不是我寫好計畫,老師你才同意我來的嗎?結果老師回應那只是個起點而已。於是這樣的過程持續了一整年,總共寫了三、四萬字的研究計畫,最終版的計畫書才終於通過Upgrade。從這個角度看,我有沒有在出國前就準備好研究方向?是有的。不過你如果要說,我的研究是不是到英國後才形成?也是對的。
不過,這並不表示我的研究方向,發生了乾坤大挪移式的變動,因為在這個過程中,老師會引導寫作方向,從形式上的文獻回顧開始,逐步引導學生梳理學術論文,但絕不會給你具體的主題,最終還是要靠自己完成一個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都清楚的完整研究提案,因此得以保持內在研究理路的一貫。我的學術之路由憲法學與行政法出發,探討公法和行政管制的問題,尤其熱衷於探索法律與行政管制的邊界與極限;我碩士論文寫的是風險社會與法治國家便是在研究,當面對這種以風險預防為目的,在時間軸線及因果關係上進行突破之管制思維,法治國家中應如何回應。
接著,從風險社會衝擊法律系統的問題意識之下,進一步去思考跨國風險乃至於氣候議題等全球風險問題,對碎片化國際法體系乃至全球治理的挑戰。氣候問題在時間與空間的大尺度,使得不確定性因果關係更難判斷。比如,如果有人上法庭提出請求台塑公司為其在德州排放二氧化碳,導致小林村被滅村、傷亡慘重,進行賠償,這時的因果關係就相當難以判斷。一般而言,我們可以理解溫室氣體排放導致極端氣候,讓人民生命健康財產受損,可是實務上法庭上並沒有辦法做出這樣的判決,而在進行相關管制或風險治理上也面臨一樣的問題。我是在這個理路下開始研究氣候議題。
只是踏進這個坑後才發現沒完沒了,像我本來是從國內公法角度切入,但是因為做了氣候變遷研究之後,我不得不去談國際公法、乃至於全球治理下的所謂全球法律。這些國際法,甚至一些沒有拘束力的決議,並不是沒有規範意義或作用的,只是比較像是原始的法律狀態,就如同人跟人之間的約定互相束縛對方。甚至有時候我們也沒有約定什麼,但是透過自己不斷的承諾,最後也能成功改變行為。但是近期,隨著巴黎協定的締結,氣候治理又出現由下而上的傾向,就法律來說,不但進入國內法層次,還有擴散進入民事法、私法,乃至於公司法、金融法的趨勢。到目前為止我還在繼續探險,繼續流浪,不知道下一步會被帶到哪裡去。
可以說我研究的理路,始終行走於各部門法律與政治(政策)、社會、經濟、環境系統間交錯的幽微地帶。雖然乍聽之下可能會覺得奇怪,但是其實整個過程都是環環相扣的。我們做研究本來就要體認到這個複雜的世界本來就是Everything is a part of everything。為了要處理某件研究議題,背後需要很多跨部門、跨領域、跨學科的知識與學習。
四、想請問老師一個比較細節的問題,在您的著作目錄中可看出您覺得氣候變遷與人權議題連結很重要,可否請您分享一下您覺得 Urgenda Foundation v.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為何值得深究?以及氣候變遷與人權保障這樣連結對台灣的啟示為何?
Urgenda案有很多有趣的、值得探討的面向。本案的被告是荷蘭政府,原告是一個荷蘭的NGO,他們向法院起訴請求荷蘭政府應該要在2020年時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1990年25%的水準,而最終勝訴的結果讓眾人大感意外。要知道,在這之前所有氣候訴訟大多都是以敗訴作結。其實這個案件不只是在氣候變遷治理,特別是減量上具有重要性,在權力分立的概念上也非常值得討論,法院是否有那麼大的權力或正當性在氣候政策上決定國家的總體減碳目標?尤其是這個案件是民事訴訟,三位沒有民選基礎的民事庭法官就決定了國家的總體政策方針確實相當特別。畢竟涉及到整體的產業、能源轉型,茲事體大。
另外,這件案子也呈現了歐洲氣候運動團體的運作模式。在氣候社會運動的社會背景下,雖然在表面上它是一個法律審理程序,但其實是以訴訟作為運動手段,跟社會運動呼應進行法律動員。荷蘭的案子成功三審定讞後,氣候運動團體繼續進擊,將同樣的訴訟策略運用到其他國家,過程中如果面臨敗訴,就運用機會上訴更高層級的法院,例如歐洲人權法院,近期亦已獲得勝訴判決。這顯示,氣候變遷與人權保障的連結已然成形,對台灣而言,不需要照搬,但確實應該認真思考這種連結在台灣的意義與可能。
五、老師的專業背景看起來偏向是法律的訓練,想請問老師是什麼原因讓您選擇投身政治學系任教?是否可以請老師談一下未來的課程規劃?
從上面的自述應該不難發現,我的研究取徑本來就傾向跨學科,除了探索多元的法律型態,也關注與法律以外的社會治理工具的協作,以及法律與政策結合的研究。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社會需要的,而公事所、政治學系的包容性能讓我充分發揮我對管制議題的研究興趣。
我目前在公事所有開設「永續發展與法律專題」的研究所課程,但也開放給政治學系高年級的學生。近期永續發展與碳定價議題十分熱門,目前在業界也看到許多永續管理與規劃的相關課程,我也曾多次受邀進行演講。但我一直在思考,大學應當開設怎樣更扎實與深入的永續相關課程,才能兼顧理論與實務。由於是專題討論課,每次開課的重點可能有所不同。畢竟永續發展和氣候變遷一樣,在當代儼然成為某種為了表達、呈現各種新的、舊的問題,所必須學會的「語言」。當各種政策主張都以永續為名,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能夠實質甄別「真永續」,可能就未必是坊間資訊提供型課程所能回答的問題。這也是這門課的核心關懷與能力培養的重點,縱使每學期所偏重的主題可能有所不同,但課程其實還是一貫的。
另外,我在政治學系也會開設行政法的課程。通常我會先觀察瞭解同學學習動機的強弱與類型再決定課程進行方式。不過因為是必修課,授課老師在一定程度之內有責任讓同學產生學習動機,讓同學瞭解課程之重要性,以及作為必修的理由。我會想盡量採用切身相關的實際案例進行教學,以問題導向的方式引起學習的興趣,讓同學知道為什麼要學習這門課程。比如說,學校規定,畢業生的離校程序一定要先將圖書館的逾期罰款、積欠的宿舍費、在學校因交通違規產生的罰款都繳完之後,才可以拿到畢業證書,該規定是否合法?在課程中我也會藉由這樣的實例,講授看似抽象的法律原則與規則。再調整一些事實條件,讓同學思考、比較案例類型之異同,訓練同學靈活運用所學的能力,並配合翻轉教學、課前學習的方式,藉以激起同學自主學習的熱情與成就感。這種教學方式是我想要努力的方向。不過下學期可能還是處於實驗階段,會再多觀察一下同學的需求與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