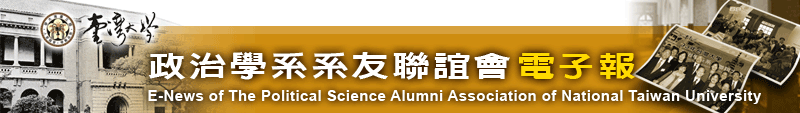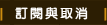臺大-北大菁英計畫第六期第一梯次心得
政治公行四 戴廷宇
六月初,從北京回來後的某一堂下課,同學問我:「北京好玩嗎?」
我愣了一下,支支吾吾,感到五味雜陳。因為在北京的兩個星期,我們上課、聽演講、遊覽、參訪、和北大同學一起生活,每一件事都是一言難盡,更似乎無法用好不好「玩」來形容。
回顧石之瑜老師在行前說明會時闡述的活動理念,是希望我們能去北京/北大「生活」兩星期,而不只是單純的「交流」。所謂「生活」,包括上課、參加社團、參與常來北大的眾多名人演講,也要去看看北大學生這群未來對手,他們怎麼生活、怎麼思考。我認為,這個活動相當成功,因為我們確實體驗了「生活」。
所以,後來我想到,或許用「值不值得」來形容這趟旅程會恰當些,而答案是「值得」。
接下來我想要分成四個部分,記錄這兩星期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壹、北大講座
我的學友是蕭堯,有天我跟他說我要去聽講座,他沉吟了一下,說:「嗯,去聽吧,北大的講座比北大的課還值得聽。」北大的講座確實精彩(但也不是全部)──不僅僅是演講的內容,還包括講者與聽眾的互動。根據我有限的觀察,發現講座似乎比課堂還熱烈,幾乎是場場爆滿,一位難求;而且發問也相當熱烈。
所以,我首先要談談北大的演講。
由於我不太熟悉北大BBS及各系所網站,所以關於演講的訊息,我大多是從三角地、農園食堂、康博思食堂前的任兩根樹幹中間得知的──因為每根樹幹各綁一條繩子,就能撐起演講訊息的布條。
北大演講訊息的公布,似乎都在一兩個星期、甚至更少日子以前,所以我走在路上時總是東張西望,深怕遺漏了哪個演講訊息:儘管如此,我還是在第三天早上,發現自己錯過前一天晚上Michael Sandel在清大的演講。
我在北大的頭五天,共聽了四場完整及兩個半場的演講。其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楊立華的「自立吾理:儒學基本價值的開展」與前故宮副院長晉宏逵的「紫禁城的建築特徵及其保存」。
一、楊立華:「自立吾理:儒學基本價值的開展」
楊立華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是因為我感受到了他因作為後進國家的一份子而產生的焦慮感以及掙扎。他表示,有些人會為了某些事情感到悲哀,但是「我們不悲哀,我們憤怒。」他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王道,「己所欲,而施於人」就是霸道。也就是說,當西方人想將西方價值強加於中國人的身上時,這就是霸道。
這讓我想到那天早上,教授《衝突學概論》的關貴海老師在講到「最危險的衝突,就是沿著文明線發生的衝突」時有感而發。關老師說:「我們現在抨擊(歐美)會有快感,但不能有自豪感、優越感,不然又是走美國的路子。」
雖然我也不喜歡美國在世界上呼風喚雨橫行霸道(例如發動戰爭、雷曼兄弟造成金融海嘯等);但個人認為,中國大陸之所以批判美國,並不是因為秉持什麼崇高的人道精神而反對該行為。其實他們心裡是認為(即便他們沒有意識到):為什麼這個行為不是由我們中國來做?
也就是說,當中國人強烈指責別人(例如歐美)的時候,說:「你們不可以這樣!」其實潛臺詞是說:「我們想要這樣,可是你們搶先在我們面前這樣,讓我們沒辦法這樣,所以我們很不高興!」
所以,過去先進國家或者挾其資金對後進國進行經濟侵略、或者憑恃其優勢軍力進行武力侵略、或者輸出強勢文化進行文化侵略,那中國現在呢?
作為大國,是否必然產生言行不一的矛盾?我覺得,或許這就是大國的必經的路子,大國必然的矛盾。
二、晉宏逵:「紫禁城的建築特徵及其保存」
晉宏逵的演講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則是因為他與觀眾的互動。
當天晚上,晉老師以「紫禁城的建築特徵及其保存」為講題。在建築特色部分,晉老師引用梁思成歸納出的九個特色,包括木梁、斗拱、富裝飾的屋頂……等等。而故宮為什麼需要維修?當然要先說明其價值,才能說服大家維修的重要性,而不是只知道這一片舊房子,可以住人可以用。
晉老師舉出三個理由──
1. 故宮是古代宮殿發展史上現存唯一實例和最高典範,保存最完整與規模最大。
2. 故宮建築群代表中國古代建築最後階段的高度藝術與技術成就。
3. 對當代社會的意義,精神支柱之一。
這個時候,有個蓄了小鬍子的男子高聲質疑:「滿清殺了多少漢人呀?你還在這侃侃而談?那不是滿人的東西嗎?還什麼精神支柱呀?」
但是,稍微有點背景常識的人都知道,儘管李自成攻陷北京時幾乎把紫禁城燒得一乾二淨、滿清之後才又重建,但紫禁城基本上是明成祖永樂年間建成的。所以,故宮到底是不是單純的「滿人的東西」?恐怕很難說是。
晉老師並未多做理會。
後來在講到修復保存故宮,可以「恢復中國的輝煌盛世」時,那小鬍子男又再高聲怒吼:「什麼(輝煌)盛世?」
旁邊有女學生說:「你讓老師講完嘛!」
小鬍子男那時候站在教室最後面,對著老師高聲咆哮:「怎麼了!我就站在這,你來打我呀!」事實上老師什麼話也沒說,小鬍子男就想要玩激烈的肢體接觸遊戲;不過從他站在教室後面一動也不動的狀況看來,他的嘴皮可能比他的拳頭硬。小鬍子男再逼問:「什麼盛世,你講呀!你是故宮院長還是滿清辯護者呀?」老師沉默了一下,之後站了起來、挺直身子,正色道:「我是中國人!」博得滿堂熱烈掌聲。
掌聲未歇,小鬍子男說:「什麼盛世,你講呀。」
晉反問:「你願意聽嗎?」
晉老師說明道,故宮從永樂十八年開始,整個明朝都是不停的建城過程;而乾隆時代的經濟國力是最強大的,是紫禁城最輝煌的時段。之後則逐漸衰敗,清出兩百五十萬立方噸磚土,可以一路排到天津。所以,要恢復的話,一定是回到乾隆盛世,而非溥儀出宮時。這番言論再次博得滿堂熱烈掌聲。
掌聲未歇,小鬍子男不斷提高聲音:「讓我說句話、讓我說句話、讓我說句話!」但是蓋不過掌聲。好不容易掌聲停了,小鬍子男逼問:「那你是同意了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了?是同意了!」
這時候出現三種人,第一種是沉默者如我;第二種是和他對吵的人,但小鬍子男說「怎麼了?不能說話了?講座不就是要讓人說話了?」某位女同學好聲好氣地勸道:「先生,別人讓你說話,你也讓人說話嘛!」第三種人則是隔在對吵雙方中間。
最後,小鬍子男被人拉出去,但還是在外面咆哮;後來則有人打電話報警。而我們的演講則平靜地繼續下去。講座結束後,我怯怯地戳了旁邊的男同學,問他是否覺得那小鬍子男可以代表多數中國人的普遍想法?隔壁的男同學表示:「這不,清朝也是中國的一部份。這是個比較狹隘的觀點。」他似乎有點趕時間,不過他臨去時又補充道:「而且你應該讓人說完,這是最基本的禮貌。」
回酒店的路上,我思考這場極具戲劇張力的講座。第一次遭嗆時,老師似乎有點在迴避問題;第二次遭嗆,才不慍不火,提出論據。究竟這種嗆聲文化想要標榜什麼呢?有不滿,當然要說出來,可是一定要採取這麼激烈的手段嗎?
想想那激動的小鬍子男,再想想我隔壁似乎頗為正常明理的男同學;我突然發現,我內心其實是想要找到能代表大陸的整體看法,可是好像在有限的時間與技術中找不到、或是說辨識不出來我聽到的哪一種意見才是。不過這種期待,就算在臺灣,也似乎是奢求了;因為,這是個標榜多元的社會,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
貳、北大課程
在北大,我聽了十門課,其中包含大堂課和小堂課。基本上上課的氣氛和我們沒有太大差別──大堂課就是老師主導整個課堂,學生少有提問;小堂課臺上臺下的互動,則會密切些。令我驚訝和感動的是,不同於我們只在學期末給老師鼓勵感謝,北大每堂課結束後學生都會鼓掌。我問他們,為什麼每次上課後都要鼓掌,他們不假思索就回答:「要謝謝老師呀!」
某天,當我們在討論下午要做什麼事的時候,北大同學衛琛說他下午要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我很好奇,說想要去聽。蕭堯說:「那你就去聽吧,反正這些東西我們從小聽到大。」於是我就跟衛琛去聽了。
上課時,除了聽老師講授的內容之外,我還不斷在心中反覆思量:「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堂課?因為,我算了一下,188人的教室中,只坐了37個人(據說這是必修)。
我們去的那個時間點(五月底),已經接近期末,所以有些課程已經進入同學報告的階段了。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我總覺得北大的日韓外籍生比例好像很多(至少比在臺大感覺到的來得多),而我在「國際政治經濟學」和「農村社會學」兩門課中聽過日韓生的口頭報告,前者是日本人使用英文,後者是韓國人使用中文。老實說,日韓生的口頭報告,著實令我感到驚訝。他們基本上就是看著稿子和投影片照本宣科,但也有極少數中文很流利的同學。我聽過一位北大本地生的報告,不用看稿、相當流暢,而且旁徵博引,我深感佩服。
在張光明「社會主義由西方到東方的演變」的課堂上,談到毛澤東認為農民比工人更高上,尊崇純樸的農民情感,反對資本主義;而毛澤東鼓勵同志要「為人民服務」,成為「高尚的人……」講到這裡,張老師開始支支吾吾:「嗯……還有什麼人?」然後有點戲謔地說:「我都記不得了,你們更記不得了。」
中間下課時,有同學查到毛澤東當初是1939年年底在〈紀念白求恩〉中,這麼說的:「……我們大家要學習他(白求恩)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有同學很嚴肅地對老師說:「這重合、重複了!」張老師語帶激賞地說:「是了,可見你的腦袋高度學術化了。但政治的語言,為了氣勢,就是這樣。」
另外,張老師還指出《建國大業》電影出了很多基本的史實錯誤,「我們的電影和學術一樣,爭相往外弄東西出來,太急了。」例如,講孫中山的電影,竟然說「孫中山,字孫文」?「太滑稽了!」羅斯福晚年會走路?宋美齡哥哥扶她?「看了都傻了我!」我覺得,不論是老師或是同學,大家都有反思能力。可是,這樣理智反省的聲音,有沒有管道盡量反映出來?
參、北大生活與同學
本系行前說明會提醒我們要有「雙重慎重」,一層是因為機會得之不易,所以要抱持著學習的慎重心情;另一層是在交往的過程中,要慎重以對。而和學友相處,就是要多問!上課,就是要多觀察!「就算內容八股,也要看他們是怎麼個八股法,瞭解北大學生是吃什麼樣的思想長大的」石之瑜教授當時這麼說。
所以我這一路上總是東張西望,多聽、多問、多觀察。
我的學友○○在最後一夜的座談會上說道:「或許是因為兩岸年輕人想得都比較開,所以我們討論了一些我們自認為很敏感的話題。」什麼是我們自認為很敏感的話題?不外是身分認同、統獨立場問題囉(雖然我們還聊了教育、計程車、食品安全、官官相護、人口控制、選舉投票、臺灣和大陸的經濟關係、美國亞太布局、蔣介石、二二八等等五花八門的話題,但是細節沒有記下來,所以姑且不談)。
關於國家/身分認同,果然○○在我們第一個晚上散步時就好奇地問:「你們是怎麼認同自己?臺灣是地區還是國家?」當然,我也早就準備好了。
我的看法是,在臺灣的脈絡下,所謂「中國」和「臺灣」的稱謂,背後已經不必然有強烈的統獨立場作為支持。我的論點是建立在政大選研中心的民調之上。所以,「統獨立場」和「身分認同」兩張圖或許可以印證我的觀點:「『身分認同』(臺灣人/中國人)和『統獨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有些脫鉤;在背後支撐『認同』的『思想』,不再是鐵餅一塊。」也就是說,認為自己是「臺灣人」(超過五成)的,並不代表他們全部偏好臺獨(偏向獨立或是儘快獨立的人,共23%),而可能很大一部份的人只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的家鄉、土地(也就是臺灣),所以自認為是「臺灣人」。
我從高中就在想:為什麼左岸似乎完整佔有「中國」這個名詞的詮釋權?雖然「中華民國」似乎也可以簡稱為「中國」,但是為什麼我們似乎不這麼認為?當左岸掌握「中國」的詮釋權(被聯合國視為「正統」)、兩岸又分治的狀況下,右岸不想和左岸變成同一個國家,可能是必然的趨勢。
同樣的,為什麼大多數右岸的我們不單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我猜想,是因為覺得「怪怪的」。何謂「怪怪的」?就是覺得該名號無法精確指稱自己。原因如上,因為「中國」被PRC佔據了。
而我好奇的是,獨立或是統一,對中國和臺灣有什麼好壞處?為什麼一定要陷在中國自秦始皇以降的大一統執念當中?
○○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好。他說他在十八歲之前很自然地認為,就是要統一;可是十八歲之後,爸爸問他,臺灣現在好好的,為什麼要拖下來和我們一樣受苦受難?○○領有港胞證,我忘記他是在香港還是廣州出生。○○告訴我,他想了想,爸爸說得也對。
當我和○○學姐提到這個故事時,○○學姐認為:他們即便跟我們說「臺獨也沒關係」,只是要讓你感到自在。可是我覺得○○沒有善意地騙我。
但是○○還是把他認為大陸目前的主流想法告訴我。他說,在理念上,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都沒敢放掉臺灣,那胡錦濤敢放嗎?沒人敢當歷史罪人呀!而在戰略上,擁有臺灣有特別的意義,代表中國擁有突破太平洋、在區域、乃至於在世界稱霸的有利地理位置。
這趟北京行,受到北大同學頗多照顧。一些北京同學第一天晚上就帶臺灣的一些同學去西門外吃烤雞翅、羊肉串、帶軟骨雞肉,相當不錯!而第一個星期六,○○和他女朋友則帶我和胡喻去後海吃客家菜──有雞、菜、牛、還有梅干扣肉,路上少不了小點心(酸奶和灌腸)。最後一晚,一些北京同學帶我們去風動樓桌遊吧,還請吃消夜。我們受寵若驚,感到熱情無以回報;但張植榮老師認為他在臺灣也有如此感覺。
肆、北京城

以臺灣的尺度來說,北京實在是太大了!「大」代表的一方面是交通時間拉長,動輒一小時;另一方面則是人多,而且似乎什麼樣的人都有。以下我要談談我在這幾個地方的所遇所想。
天壇是個很有活力的大公園,除了遊客之外,也似乎有附近居民(大多數是中老年的男男女女)在這裡從事許多活動──合唱、跳舞、下棋、圍在一起踢毽子、做體操。所謂「做體操」,不是健康操,而是運動會上那種撐來盪去的體操。
不過在順利進入天壇公園前,我買票時遇到了一些困難。
我拿著臺灣大學的學生證,希望能買學生票,但一號窗口告訴我要「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的。或許是因為聽先前來過大陸的學長姐的說法,我預期自己理所當然能夠買學生票;但實際上發現,拿著臺灣大學的學生證就以為能夠無往不利享受優惠的心態並不正確。由於我抱持著這種理所當然的心態,說來也難為情,但在被拒絕的時候確實就是惱羞成怒。在那麼一瞬間,我差點脫口而出:「你們不是說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嗎?」好在我的嘴巴總是動得比腦袋慢,我認知到:這對對方來說,可能是過分的要求;而且我是來交流,不是來製造糾紛、樹立敵人的。
我把錢和學生證拿了回來,說聲謝謝。換到二號窗口,也是這樣,但是售票員比較溫和。售票員背後剛好有個長官,她問我大幾,我說大三,並解釋說所謂的民國七十九年,加上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就是西元年份一九九○。最後長官對售票員說賣了賣了。
我應該檢討我自己。
天安門前廣場佔地廣大,遊人如織。
從開始排隊到買到票的三十分鐘,我發覺五湖四海的口音,還真的很難完全聽得懂。我手才剛碰到剛買到的票,後面兩三個年輕人的其中一個就急著把錢塞進窗口,我無法理解這樣的行為。是因為害怕被插隊嗎?
一開始看到太和殿的金碧輝煌,我覺得很氣派;但後來看到一些比較次要宮殿的古樸,突然覺得太和殿的金碧輝煌不那麼值得讚許了。我不知道古蹟應該要保留其原貌,還是要維護得金碧輝煌?或是這兩者其實不衝突?
有些遊客不太尊重古蹟。我覺得,我們來這裡腳踩步踏,對古蹟就已經算是一種慢性的破壞,但還是有人要這裡敲敲、那裏拍拍,這裡打打、那裏摸摸,似乎不如此就不過癮。
通常看到這種狀況,有人就會輕蔑地嘲笑說:「哈哈,你看吧!對岸就是文化素質低!」而潛臺詞就是:「你看,咱們臺灣多們文明!」可是我並不覺得臺灣有「文明」到足以批評別人。當大家都沉浸在捷運(大致上)有秩序地先下後上、搭手扶梯時立於右側的美妙現象時,我在中正紀念堂幫忙某大型活動時看到的卻是:人們總想突破那圍起來的紅線區域。
北京,晚間七點,夜未降;七點半,天才將暗。對我來說,北京空氣實在很乾,都不下雨實在是感到不太對勁;直到我們離開的前兩天,才淋漓地下了場帶有濃濃土味的雨。
初到北京的前兩天早上,我都被清晨上班的喇叭聲吵醒,瀕臨崩潰邊緣;後來卻也習慣了,甚至還很開心地告訴自己:都不用調鬧鐘耶!而在北京過馬路,得全神貫注,實在馬虎不得──特別是在那種找不到紅綠燈規律的路口。例如,橫越海淀橋底下的那個路口,我至少走了七天,但我還是參透不出它的規律。
所以,我一方面無奈地發現:有時候必須入境隨俗闖紅燈,不然根本沒有辦法過馬路、或是要等好久才能過一個路口;另一方面驚訝地發現,原來要開啟在大馬路上闖紅燈的心理開關是這麼容易。但是我還是覺得找不出規律的交通號誌要負比較大的責任。
在我搭地鐵的時段,北京地鐵和臺北捷運有差不多的人口密度。可是,為什麼在北京會覺得比較不舒服?在地鐵上,總覺得身邊的人怪怪的、感覺就是不太舒服。是因為不太信任其他人的關係嗎?是因為北京太大了、好像什麼人都有嗎?我嘗試要去信任身邊的所有人,但還來不及建立信任,我就離開北京了。
有次在地鐵上,人有點多,但彼此之間還有些空隙。突然,我聽到有人唱歌。等到歌聲稍近,我才發現歌聲是來自一個個大約三十來歲的男子,他用手撐地前進。他唱道:「一家孩子在外,月兒圓呀月而圓呀……」老實說,歌聲還真不錯,嘹亮、乾淨。唱了一段,他說:「謝謝在座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我祝你們全家幸福、身體健康。」
我感到很震撼。
我們最後一晚搭計程車回酒店,後來○○學長和我們分享司機說的話──「啊你們從臺灣來呀!那你們快點回去吧!」到大陸三次,在有限的樣本中,我發現:歡迎我們的都是中產階級以上,而小老百姓都叫我們趕快回去。
回到臺北,有好一段時間,走在街上都會不自覺地拿臺北和北京比較。結論是:還是臺北好。也不是說北京有多糟、臺北有多好,其實各有特色,但或許是因為我習慣了,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臺北。對我而言,我是離鄉離土,才更愛鄉愛土。臺北是我的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