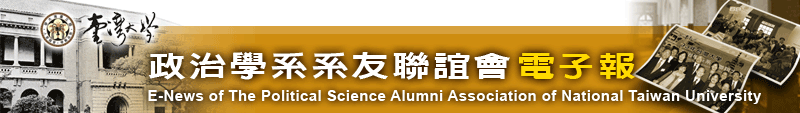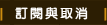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研究」/「人生」 -專訪系友 吳玉山院士(69年班)
訪談人:江軍(政研二)
江軍(Q):老師在本學期初曾受邀至社科院,並給了新生們一場入學演講!想問問老師,在畢業多年後,看著這群學弟妹,當下的心情如何?

吳玉山院士(A):你也曉得,我那場演講的題目是「研究人生」。當時想著,這些年輕的學弟妹剛進台大,學習的社會科學領域跟人們在社會中各種活動息息相關。又想,他們進大學後,究竟在台大的社會科學系所裏頭能獲得什麼東西?所以就以研究的心情,去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我們在大學裡學習到的,這些個理論啊、知識啊,主要目的是去培養我們具有研究的傾向。對於社會現象,能夠比較冷靜的去做觀察,而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會很情緒性,或者是理盲。我覺得這是社會上需要的,也是台大的社會科學訓練,應該要給予同學們的。社會科學的特性就在這,不像你學了醫學,就要做醫生;如果學了建築,就要做建築師。它跟理工、生命科學最大的差異點是:它跟你將來所從事的工作間沒有一對一的對應關係。那在這種情況裏頭,一個一般性的研究傾向,可以有助於他從事各行各業的工作,對他來講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再算一算,自己是1976年進台大,做這篇演講時是2016年,整整40年。40年以前,我也是坐在下面,跟這些年輕學生一樣。過了40年,我的感覺是什麼?能夠有些想法,對他們有些幫助的,就盡量提供給他們。
Q:您有特別提到,當初進台大時,是有一個動機,乃至於激勵的因素,讓您選擇台大政治系。能不能請您談談當時是什麼原因讓您進了政治系?
A:其實蠻清楚的。當時是在國家政治局勢很困難的時候─1970年代末,各種挑戰紛至沓來。所以那時候不但想要念政治,而且還要念國際關係組,就是覺得當時受到最大的衝擊就是來自這個方向。果然就是在念大學的時候碰到了中美斷交,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所以,蠻有趣的,那時候也沒想到就業是怎麼樣,沒想到將來究竟從事什麼行業,只想到說,糟糕了,國家碰到這麼大的衝擊,你能不能做點什麼事情,這個好像是最直接,最密切的。
其實我最早的興趣不是在政治,是歷史。我對歷史有天然的興趣,常常覺得在看歷史文獻,甚至於在讀歷史小說、看歷史相關的電影時,感覺特別深。我原來以為我會成為歷史學者,但就是在那段時間,讓我覺得,我應該要去了解政治的情形是什麼樣子。其實也就是因為那種想法,我進了政治系以後,最大的興趣是研究中共跟俄羅斯,然後我去學俄文,這些都不是什麼「因為對俄國的文學有興趣啊」,不是。因為我覺得,對我們的壓力、影響和衝擊,就是來自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的根源是俄羅斯,那我要把它搞清楚。是非常務實的!而這種想法,我覺得一直到今天,都還有影響。就是說,其實大局並沒有變,你面對的是一個改革的中共,他跟你最大的不一樣,就在於制度跟意識形態。那個的根源,其實還是在我有興趣的那一塊。所以我整個學習和研究的取向,是這樣來的。
Q:那在這樣的情況下進來政治系,應該有很多對您有所影響的師長或事件,能和我們分享幾個有著深刻印象的嗎?
A:如果講事件的話,就是我們跟美國斷交。我還記得那個時候,美國特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到台灣,來跟蔣經國總統報告這件事情。其實也就是送個通知來告訴你,我跟你斷交了。我們同班同學,一大堆人就跑去機場,丟雞蛋啊,什麼的。諸位要知道,1970年代末,在台灣是沒有這種事情的,做這件事情是絕無僅有,或許是這些學生這輩子第一次。那,政府確實沒有去阻止,但也沒有要動員我們。當時就是自然的有這種心情,覺得為什麼一個忠實友邦,會對我們做這種事。那時對於國際關係的想像是非常天真的,用很多中國式的人情義理去做推論,而不是去了解國際政治的真實面貌究竟是怎麼樣。現在想想,很多東西是認識不夠的。但那是一個很自然的情緒。所以,我想對我們這些,那個時候(1976-1980)念大學的,那個事件大概是衝擊最大的。在那之後,我們在國際上就陷於孤立。我現在想起來,有一個感覺,如果我們在國際上不是陷入那麼孤立的情況的話,現在的台灣對於自己的觀點,對於整個國際世界的了解、自我的期許,都會不一樣。那是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老師們的話,有好幾個老師對我影響蠻大的。因為我的興趣在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和蘇聯。那時候有位老師叫魏守嶽,這位老師,一般的同學不容易和他親近,因為他口音重、看起來嚴厲、對學生的要求也比較傳統。他教的是各國政府,而那時候的各國政府,對各國的憲法、法律啊,是比較著重的。不是像後來變成各國政治,或者是比較政治。但是現在想想看,如果你對一個國家的基本體制不了解的話,那你真的是什麼都不知道。這是重要的基本知識,但他自己的興趣是研究蘇聯政府。所以從他那裡,我學到了很多共產黨政治體制的東西,一直到現在都很受用。那魏老師呢,因為上課的時候,跟大家有個距離,而我是那種,怎麼講呢,就是,最乖的那種學生。每一次來就反正坐前面中間。那他口沫橫飛地對全班講話,全部的人就坐得像ㄇ字型一樣,盡量往旁邊和後面坐。變成他對我一個人講課,然後周圍沒有其他的學生…一個,非常奇怪的情景啊。
但一直到現在我很感謝他,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當他教到美國政治的時候,他會把美國最高法院歷史上重要判決都印了,讓我們看。那時候覺得苦不堪言:我們沒有美國政治的背景,對於那些法律詞句也不甚了解,然後他有可能隨便挑一個案子來考你,例如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是怎麼開始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是什麼等等,感覺很痛苦。我們那時候還特別組織了讀書會,一份一份地研究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比如說現在系裡頭的石之瑜老師啊,立法委員陳學聖啊,我們都是在一個讀書會裡的。可是我覺得後來真是受用無窮啊。這是一些死功夫,一些必須有的知識基礎,我覺得透過他得到了很大的收穫,所以我一直記得他。但他跟一般的同學其實不是那麼親近,我跟他也並不親近,但我很願意接受他的訓練。後來我寫的筆記,就我所知,很多人都用,好像還傳了幾屆。所以他是一個對我影響蠻大的老師。
還有一位老師,是不久前才從系裡退休的蔡政文老師。他那時候剛從比利時魯汶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回來,是一位年輕的歸國學人。然後,嗯,應該是我在大四的時候,修到他國際政治的課。你可能也曉得,同學們對於剛回來的老師是最有興趣的,就想看看他能帶來什麼新的觀念或看法。他寫了一本書,是講核子時代的國際關係特質,把核武怎麼影響國際政治闡述出來,我們覺得是很新穎的觀點。蔡老師多年來一直都在教國際關係理論。我從他那裏獲得很多東西。所以一個年紀非常長的老師,有非常傳統的教法;一個年紀最輕的老師,帶來一些新穎的觀念,他們兩位給我的影響都很大。
蔡老師跟我還有一個重要的關聯,是我在1991年的時候從柏克萊(UC Berkeley)拿到博士學位回來,剛好蔡老師那時已經做系主任了,是他開始聘我到政治系教書的。剛開始的時候還是客座副教授,之後才轉成正式的副教授。所以蔡老師對我的淵源很深。他教政治社會學,課程調整後就交給我來教。我也是一直兢兢業業,不敢砸了蔡老師的招牌。
Q:關於研究生活,您常說家人是佔有重要地位。能否請您談談這些「重要他人」在您研究路上的影響?
A:我想,對於我從事學術研究,產生最大作用的是我的父親。那個影響可能是潛移默化的,自己不會感覺到。舉個例子來說,在那個比較封閉的時代,我會接觸一些和國際共產主義相關聯的書籍,原因就是,在我們家裡頭,有很多好大的書架,裏頭擺滿這一類型的書,我沒事就跑去翻啊。
我父親從來沒說過希望我做他自己做的研究,他是歷史學家出身的,寫印度史,寫甘地,也寫東南亞史,是一位區域研究專家,一個歷史學者,在台大、政大、師大都有開課。他口才很好,學生滿天下,後來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政大國關中心的前身)、召開中美會議這類學術活動。我覺得我受他影響絕對是最大的。至於其他的人,我的母親啊、太太啊、小孩啊,他們給了我一個supporting environment,讓我可以很放縱地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我周圍的環境給了我很好的條件,我很感謝他們。
Q:您剛剛說到,您對研究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志向,就是「當老師」。那,您應該對「老師」或是「教學者」,有一個想像,可以請您分享一下那個想像是什麼嗎?
A:嗯…這個可能是從小就開始了。很多人大概從小也想當老師。為什麼呢?因為老師有學問、老師有權威、老師受尊敬。你在學校裏頭,唯一的model就是老師嘛,對不對?如果是一個好老師的話,他的幾句話,可能給學生產生一輩子的重大影響。但如果是一個不好的老師的話,他的不負責任,或是懈怠,也會讓學生一直記得「天啊,我們以前有一個很糟糕的老師」。
從小我就在想,將來如果做老師的話,是很有意思的事。然後我又覺得,做學問、做研究是最快樂的事,但是你一定要能夠和人家談。這裡頭當然包括跟同儕談,還有包括跟學生談。學生有個特性:學生不是那麼地被琢磨過,但也因此有清新的想像。你常常可以從跟學生的討論中獲得很多的靈感或啟發。所以那本身是個非常愉快的事情。我在大學教書的心情就像喬丹(Michael Jordan)一樣,感覺是別人請我做我最喜歡的事,真是何其愉快。
我第一次當老師不是在大學,而是在空軍官校。我是在空軍官校服教官役,所面對的學生,是很特殊的一群學生。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希望成為一個戰鬥機飛行員。他的學科不見得要求那麼高,但是反應非常的靈敏,視力要很好。他們要修的東西很多。包括從我教給他們的歷史的、理論的、國際現勢的東西,到流體力學、飛機的結構力學等等,這些他們都要學,才能成為飛行員。我在跟他們互動的過程中非常愉快!我第一次感覺到,如果你能融入他們,他們就能夠接受你;你跟他保持距離,他們就是遠遠的看著你。我當時只是預官,年齡跟他們又很相近。然後,你可以想像,我那個時候─其實可能現在還是這樣─是有很浪漫的理想主義的,覺得這些年輕的飛行員要保家衛國,做的是很值得尊敬、很偉大的一件事。所以我跟他們的感情很好。那時候就知道,我跟學生相處可以有很大的成就感。我帶著這些飛官參加辯論比賽,他們中間有好幾位一直到後來都當上中隊長、大隊長了,還是很好的朋友。
後來到台大了,更是這個樣子。因為,這是我們國家菁英中的菁英,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有自己的企圖、想法、發展,這真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我那時候是考公費出國的。有些人雖然是公費出國,但他寧可給國家賠錢也要留在美國。我一方面當然因為是公費,另一方面我在想,如果我一輩子是教育美國的學生,教育美國的菁英,我的成就感絕對不像我回國教育我們自己的菁英來的滿足。別的不提,就這一點,我絕對不會待在美國,所以我想教學對我的影響是蠻大的。
Q:那,從學生開始,到後來的教學者,一至於現在您成為了中研院院士。一路走來,可能有很多抉擇的過程。那我想分成兩部分談,第一是,當年所想像自己可能成為的那個模樣,跟現在的成就,兩相對比,您覺得自己做到了多少?第二個部分是,一路走來可能有很多抉擇,當然做選擇時勢必放棄一些東西,那有沒有一些東西,現在想起來會覺得「啊,有點可惜」?
A:雖然我們一開始有講到說,社會科學這一塊,你不一定學什麼,就會在哪個位置上。但是對我來講,可能比較特殊的是,我真的是做了我自己本來就想做的事情,所以就大方向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多的驚奇。我是在台大政治系國關組畢業,之後去念政大東亞所。完了以後當兵,兩年後出國。在Berkeley念了7年,回來在台大教書教了11年,然後到中研院服務,同時也是台大的合聘教授。所以一路過來,如果說是比較沒想到的曲折,第一個應該是:我能回到台大教書,這對我來說當然是最好的事,但這是不確定的,你永遠不知道這個機遇是不是在這裡,能不能通過考核,在系裏頭的甄選過程,能不能成功。我很幸運能夠做得到。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點。
到中研院來,則是完全沒有想到。因為我既然喜歡教學、喜歡研究,在台大政治系,又回到母系─這裡有最優秀的同學─我大概就不會動了嘛,對不對?那麼會發生這個事情是因為中研院當時要籌備政治所,想以經驗政治為主。台大政治系的胡佛老師,就是倡議在中研院成立政治所的主要人物。當時要物色一位政治所籌備處的主任。中研院有一個很特殊的習慣,要設所一開始要先成立籌備處。之後從籌備處到正式成所,中間平均大概需要9到10年,所以籌備處主任是非常重要的。我那個時候在台大已經教書有11年的時間(1991-2002)。這段時間,在國科會和教育部獲得了一些研究和學術的獎項,所以後來我成為了國科會政治學門的召集人。我猜可能是這個原因,中研院找到我,要我到來籌備成立政治所。
這是一個完全沒有想過的事情。當時是朱敬一院士(時任中研院副院長)來找我,請我擔任政治所的籌備處主任。那時候我想如果我能持續在台大教書,另一方面,又能夠在學術界裡面創立一個重要的機構,會是最好的。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能替我們國家的政治學做一個或許絕無僅有的貢獻!因為中研院成立政治所,也就只會有這一次,而中研院當然是極為重要的學術機構。所以我那時候仔細的考慮後,就決定答應,但前提是我要能夠繼續在母系教書。
因為我這麼熱愛教學,所以那時候想的是,我到中研院來籌備政治所,但是絕對不要以放棄教學、放棄指導學生論文、放棄我在台大政治系的工作做為代價。現在想想,政治系能夠讓我繼續在系裡擔任合聘的老師,是非常重要的。我不認為只是一個人埋頭做研究會很完整、快樂,我一定要有學生在一起,才能夠教學相長。不過當然,這樣安排的結果也會把自己弄得很累,但卻是值得的。所以你問我有什麼意外?我覺得去中研院創所是我最大的意外。其他的話,幾乎就是美夢成真。
Q:那,剛剛您有提到,關於您當時,80年代,有著時代的挑戰。到了現在,我想時代性的挑戰,有變也有不變。能否請老師談談,您覺得在現代,對國家,乃至於將成為社會中堅的年輕人的挑戰為何?
A:其實這麼些年來,我們的基本處境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所以年輕人的挑戰就是兩個部分,一個當然就是自己的生涯規劃,如何讓自己有個能實現自己理想的工作環境、成家立業,等等。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比較總體的,是台灣現在所面臨的狀況。其實台灣從來就沒有「舒服」過啊!我們一直有「是否能存在」的「危機感」。即使是在我們還有國際地位的時候,我們所面臨的是,隨時可能受到對岸的攻擊。後來我們丟掉了國際上面的身分,跟這些對外的關係,挑戰當然大的不得了。後來是靠著經濟上面的表現,能夠獲得一些突破。那現在當然,經濟這一塊也變成了大問題,但是,其實從頭到尾,台灣一直都沒有個很好的發展環境。我們一路能夠走過來,就是因為在困境底下去激發出拚命的精神。可能是老一輩的人都有的感覺吧,覺得如果沒有那個拼命精神,就會沒有辦法的。接著就會擔心,我們的年輕一輩,是不是還有那種精神。我們的困境一直在,但所有我們能夠講成是成就的東西,都是拼命克服環境的挑戰所帶來的。所以,我覺得我們得要有危機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被視為理所當然。然後,不管是個人,或者是整體,如果我們要有所獲得,可能要能承擔成本。也就是有些東西是要犧牲的。什麼糟糕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所以你要做好準備、隨時擔心:每天每時兢兢業業,很緊張地在保護、維護自己現有的東西─它隨時可能會丟掉。我想我們將來還會繼續受這樣的挑戰。這挑戰非常清楚:對岸這幾年的崛起,兩岸關係該如何處理?我們自己裏頭,態度、觀念、看法,彼此是不一致的。你如何去維護住一個健全的民主體制,要讓它能夠運作,也要讓它能夠有效能?那這裡頭有好多困難的選擇,我們必須去做。
我是覺得,危機感可能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危機感是用在,當你追求自己價值的時候,想辦法能夠讓自己做到最好。你不一定是走哪個方向,但特別是台大的學生,應該可以惕勵自己:「我不管做什麼,我一定要在那個領域裡,做到讓人刮目相看。」
Q:您在院士訪問中,有提到一句話,我印象蠻深刻的:您覺得自己成為院士,「對政治學有打氣效果」。是否也正基於您剛剛提到的原因呢?激勵自己去為下一代做點什麼?
A:我們在自己的學科裏,可能不是那麼感覺到,但是當你在面對台大、中研院各個領域裏頭最尖端的菁英時,首先你會覺得,人文社會科學是弱勢,理工跟生命科學是強勢,我想這不僅在台大是如此、在中研院是這個樣子,在整個學術環境中也都是這樣。
第一流的人才,應該來念文組,特別是念社會科學。原因是,這一塊才真正是一個國家社會能不能夠有競爭力的關鍵因素。我們有一群在實驗室的菁英跟專家,這部分我覺得台灣訓練了很多,可是,如何把這種菁英的知識組織起來,讓他能夠成為有利於社會人群、有利於增加國家競爭力的資源,這個是靠社會組織的規劃、政治經濟體系的運作,是這些個專家無能為力的地方。那麼,為什麼在這個社會裏頭,研究「物質世界」和「自然世界」的專家們好像很重要,可是去探究人文社會的專家,反而不是那麼重要呢?很簡單,人文社會的專家所提供的是公共財。他們所提供的研究對整個社會有用,但是沒有人願意購買它。因為大家都是為了私利,所以希望購買你的知識,能夠幫我創造在市場上能夠銷售的產品。公共財的定義就是在於,它所提供的貨品或服務是很重要的,可是你沒有辦法把它變作是私有的財貨,然後靠著它來獲得利益。就是簡單的這一句話:它的知識性質,是重要但不可販售的。如果我發明了一個技術,可以減少冷氣的能源消耗,這個當然很有用啊。廠商就可以把它拿來做低耗能的冷氣機,接下來拿出去賣,大家就可以省電費。這整套就是市場邏輯,對不對?如果我現在設計出一個好的選舉制度,能夠反映民意,同時也能夠創造一個有效率的治理體制,誰要買?可你如果沒有那個東西的話,你的政治經濟是不上軌道的、各種群體之間的衝突是無法解決的。社會一團亂,一天到晚在示威抗議、暴動打架、政變,那些物質的東西研究再好,有什麼用?以今天的情形來講,兩岸關係沒有處理好,我們連存在都發生問題,還能去研究奈米嗎?所以我常常會覺得我們做的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沒有被社會充分地看到。這是因為社會會短視,也是因為我們沒有讓這個社會真實的理解到,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所以,若是當選院士能夠凸顯這一塊,讓大家知道、重視這一塊,能夠使我有較大的能力去提醒大家、做一些發聲的話,我覺得這是重要的、有意義的。
Q:最後,想請老師對本系的學弟妹、乃至畢業的系友說幾句勉勵的話?
A:「多帶一點理想主義…傻傻的理想主義」,還有一點,「多把別人想得好一點」。這兩個東西要合到一起才行。多帶一點理想主義的話,我們能做好多真正能讓自己快樂的事,因為你不是在必然的邏輯底下,必須要做很多事,而是你可以做一些衷心喜歡的事情。這當然是當大家行有餘力的時候最能夠這樣做。例如在做助理教授的時候,說不定滿心想的是升等,那麼你到了副教授、教授的層級,就該好好去做一些你覺得值得做的、但不見得能累積你的積分的研究吧!
這種理想主義能夠激發你去實踐理想,但是必須要跟一種比較容易能夠接受別人、或者預先把別人覺得是「他一定有他好的那一面」兩者連繫在一起,才能夠發揮正面的作用。因為我覺得,我們容易很犬儒,很容易批評、挑剔;很容易看到別人做得不夠、不足,很容易懷疑人家的居心。
我有點怕聽到一個東西叫做「可以合理的懷疑」。通常講這句話,接下來就是要講說,「那個人是壞蛋」,或者「他是齷齪的」。當然你可以合理的懷疑,而也可能那個人真的是壞蛋,可是難道不可能那個人並不是那樣嗎?我覺得,我們把很多事情預想的很糟,背後的心情是想保護自己。這樣的話,我就不會因為自己太過於善良,所以被欺騙。可是當我們每個人都用最大的心情在保護自己的時候,你知道,人與人之間的猜忌、敵對、懷疑、嫉妒、仇恨…會帶來多大的負面效果嗎?會把這社會搞成什麼樣子嗎?會讓你覺得這個世界多醜惡嗎?又會多影響到你對別人、對自己的觀感跟看法嗎?所以,有理想主義,也要能給別人benefit of doubt(姑且信之),我覺得這兩個心情能夠連在一起,是「快樂做人」一個很重要的前提。給別人benefit of doubt的意思是,既然我不確定,我寧可相信他是好的;我說不定會吃一點虧,但長期來說,對總體而言,每一個人都會更好。我舉個例子─我周圍左右的人都出現過這種事─學生寫字寫太好了、作文寫太好了、答卷答太好了。老師不相信,而且處罰你。為什麼處罰你?因為你怎麼可能寫那麼好?因為你很糟啊!有沒有這個可能?有啊!可是萬一、萬一這個學生就是在那一次,他特別地認真、用心,他其實很期待老師在那個場合能夠肯定他、鼓勵他。如果你肯定他、鼓勵他了一次,這個人可能就因為那一次而脫胎換骨,變得完全不一樣。那你是要給他benefit of doubt,還是「我合理的懷疑」?在合理接受的範圍內,你多給一些人benefit of doubt,可以讓整個世界變得美好得多。我覺得在我們成長時代的社會,跟現在的社會,就有這點差別:我們的名嘴啊、報紙啊、傳播媒體啊,常常用尖酸刻薄、充滿懷疑,全部都是不信任、互相攻擊的方法在處理人際關係。我們那個時代沒有啊!所以,何妨給人家benefit of doubt,而不要「我可以合理的懷疑」。然後另外一方面就是,發揮一點理想主義,能夠的話─也不要太非現實─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歡,而不是那麼功利的事情。然後,感覺會很好。台大的學生,就算現在還不是,將來也都是這個社會上比較有能力的人。多做一點這種事情,會把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往那個方向帶。我覺得,會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