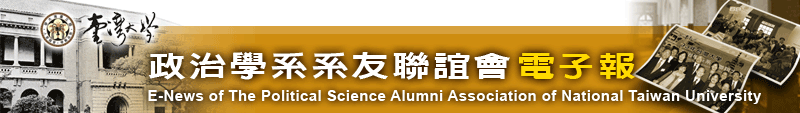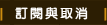錢復院長(45年班)與青年學子分享人生經驗
文字整理/許芳暄(政論三)
圖/天下文化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與天下文化於 2020 年 9 月 29 日(二)共同舉辦「錢復院長與青年學子分享人生經驗」活動,活動當天約有150位師生參與,天下文化也在活動現場免費贈送《錢復回憶錄・1988-2005台灣政經變革的關鍵現場》乙冊給與會者。
活動開始先由本系張佑宗主任代表致詞,其後便由天下文化代表吳佩穎總編輯致詞。致詞結束後,接著進行贈書儀式。本系由張佑宗系主任擔任受贈代表,感謝財團法人富蘭克林文化公益基金會劉吉人總裁及錢國維先生贈書近1,000給予本系。讓本系青年學子有機會透過閱讀《錢復回憶錄》,厚實自身的歷史觀,並進而開展國際視野。
贈書儀式結束後,由中央研究院朱雲漢院士擔任主持人,朱院士與錢院長透過對談的方式進行。錢院長將自身的過往經歷娓娓道來,談到在外交事務交涉上的趣聞,並分享四十餘年的公職生涯經歷的信念。座談結束後的提問時間,在場青年學子的提問相當踴躍,問題從國際局勢涵蓋到自身能力的養成教育問題。並請錢院長跟學弟妹分享自身的經驗,若未來有意要從事公職,需要培養什麼樣的能力、技能以及用何種心態還面對公職人生。座談與提問時間結束後,便進行簽書時間,大家瞬間變成小粉絲,興奮的拿著書跟錢院長合照,活動即在排著長長的簽書人潮中結束。本次活動也請到臺大演講網協助攝影,歡迎有興趣的系友日後到臺大演講網觀看,以下先簡述當天活動內容。
錢院長:我跟臺大政治學系有很深的淵源。68年前,我考進臺大政治學系,畢業後到美國讀書,回國後很想回臺大政治學系教書,但是當時先父錢思亮在臺大當校長,所以我只有在政大兼課,沒有到臺大教書。五十年前(民國59年),先父離開臺大後,臺大政治學系立刻就聘我擔任兼任教授。兩年後,我就到行政院新聞局做局長,因工作的壓力太重,沒有辦法分身到臺大上課,因此辭掉兼任教授。直到我擔任國民大會議長時,臺大又聘我當兼任教授,教了兩年之後,我又被提名監察院院長,監察院負責全國軍公教機構的政風,特別是對於有違法失職的要彈劾、糾正、糾舉。所以任監察院院長期間,我不能在臺大教書,不然別人會指控這中間有不妥當的情形。今天有機會回來,我也很開心,我也很感謝這幾年臺大政治學系的同學都有辦「政治人之夜」,每一年都請我擔任貴賓,要我主持政治人之夜的討論會,除非遇到出國,或是健康不允許,每一次我都一定準時到,所以我對於臺大政治學系有一份特別的感情。這一次出書,天下文化要做公益贈書,感謝劉吉人總裁和錢國維總裁兩位一口氣就捐一萬本給所有國家相關的圖書館。我有提醒兩個單位要多贈送一點,第一個是臺大政治學系,第二個是政大外交系。因我前後在外交部工作了三十幾年,我的同仁來自外交系的有一半以上,所以有今天的公益贈書論壇。我也感謝天下文化請到我尊敬的好朋友朱雲漢院士來跟我對談,現在我是學生,請朱教授出考題。
朱院士:謝謝院長,他是我最尊敬的前輩、大學長,而且我也很幸運能在院長身邊工作,得到身教言教,受益良多,以前他是我高山景仰的偶像,有二十年的機會可以在他身邊學習是非常特殊的際遇。對錢先生各方面的推崇、各方面的肯定,我就也不在這邊多加贅述,那我有一句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學校、一個學系的高度並不是由這個學系的老師所定義的,而是他們培養的學生、還有這些學生的成就所定義的」。事實上,錢院長把臺大政治學系帶到高峰。在這邊我也想跟大學長報告,臺大政治學系有很多第一志願來報考的新生,錢院長傑出系友、崇高的成就,讓臺大政治學系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我們學校裡面,臺大政治學系是很熱門的學系,包括主修、雙主修和輔系的人數都很多,這也是近幾年很大的成就。我想先拋磚引玉提出幾個問題,向大學長請益。因為您先前有提及您跟臺大政治學系的淵源,現場有很多年輕朋友,有關於「生涯規劃」的疑問。如果您可以回到當初選擇學系的時候,是考上臺大政治學系就要當外交官,還是人生有很多際遇,不見得是可以規劃的。
錢院長:首先,我選臺大政治學系為我的第一志願是有原因的,我五歲的時候,我的先祖當時是上海特區地方法院的代理院長,受到日本政府和漢奸共同策劃的行刺,身中四個子彈,夏天穿著白色的袍子回家,身上的袍子被染成紅色的,我就這樣親眼目睹我的祖父離世,他當年只有五十歲。我很小,但是我就想為什麼我的祖父就這樣離世,這個理由很簡單,他擔任上海特區地方法院的代理院長,什麼是特區?就是租界。什麼是租界?就是滿清政府非常無知,沒有國際關係、國際法、外交的概念,閉門造車,以天國自居,認為其他國家都是來求我的,而且武力又很脆弱。所以很多列強來打仗,每打一次仗,就輸一次,輸一次就簽訂一個不平等條約,一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讓列強劃定租界範圍,給列強在租界裡面有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這許多讓我國蒙羞恥的作法都是因為滿清的官吏不懂外交、不懂國際法所導致的,所以我就立定志向,未來一定要讀外交,一定要從事外交工作,一定要用國際法來維護我國的權益。國際法是很重要,但是你們閉起眼睛想一想,在現在的國際社會,國際法行得通嗎?美國的領導者上任之後就把好不容易簽訂的氣候協定(巴黎協定)撕毀,條約都可以撕毀,那還有什麼國際法可談呢?很可惜國際法不被重視,但國際政治和國際關係還是很重要,這個不能夠忽略。每個國家處理外交事務,一定要本著國家的基本利益來訓練一批優秀的人才來辦理外交,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現在是新生,我還是會有同樣的選擇。
Q:錢院長很有語言的天賦,英文的造詣很高,我想說您創下的紀錄是沒有辦法被打破的,您曾經為蔣總統、蔣夫人做英文翻譯。當時您做翻譯的時候,蔣夫人就坐在旁邊,您是如何去克服這個壓力的?

錢院長:很榮幸這些長官對我有厚愛,覺得我可以信賴。蔣夫人坐在蔣公旁邊對我的壓力很大,因為我的英文比不過蔣夫人,不只比不過,而且還差很多。但是我有一個長處,也就是在我之前,蔣夫人測驗了好幾個可以替蔣公作翻譯的人,但沒有一個人通過,而我通過。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從小到大都是被我媽規範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能走錯一步路、不能說錯一句話,用字遣詞要小心,我學的是很規矩的英文,不敢說Classical,但是是Classroom英文。蔣夫人聽我翻譯後,就告訴蔣公說他的英文就那麼一回事,馬馬虎虎,但是他的用詞非常好,符合你的身份,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講多少,他翻多少,不會多一個字,沒有少一個字。那個時候的我年輕,我的記憶力強。我也幫陳誠副總統做兩次的翻譯,一次是石門水庫開始使用;一次是故宮博物院啟用的。陳誠副總統沒有講稿,隨隨便便講了二十分鐘,我也隨隨便便翻譯了二十分鐘,但是下面聽得懂的人都說,他都背起來了!事實上不是,我就是強記,馬上把陳副總統說過的話翻成英文。我下面坐的美國大使不會中文,他們先聽中文,再聽英文,他們開始對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因為做翻譯最怕替元首做翻譯,我一定要忠實於他們的講話,不能把我想要的話講出來,兩邊都是一樣,我要忠實地。有時候忠實翻譯是很難的,比如說蔣公有時候會突然想出一些事,對美國很不開心,就說幾句重話,我到底要翻到什麼程度,這就是我必須要思考的,為國家的利益,我是要照翻?還是要委婉一點地翻?那我多數的時候會把它變得委婉一點。所以做翻譯是溝通兩方面,溝通就要希望兩方關係可以增進,不希望破壞。這就是為什麼有時候講的重話,我不會照原文字翻譯出來的原因。
Q:您是在1982年赴美擔任代表,在美國六年多來,受到美國政壇各方高度的肯定,回想起來,那段赴美的任務是一個很沈重的壓力,因為當時中華民國和美國是已經沒有外交關係,但是也是在美國和對岸關係正常化的蜜月期,大戰略裡面還是要拉緊北京以對抗、平衡蘇聯。當初還沒有進入後冷戰時期,當時很多國際的輿論對中華民國不見得非常友好,當時國內也面對政治轉型的各種尖銳挑戰。請您分享一下,您在美國這六年,怎麼從谷底,一步一步地把臺灣和美國的關係擺在比較穩健的基礎上,並進入互信、厚實的階段。這個過程一定非常辛苦、辛酸,因為當時臺灣畢竟沒有正常的邦交關係,您在回想這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錢院長:首先,我想說的是為什麼會派我去美國,1982年7月1號,我從歐洲訪問回來。我在歐洲訪問的途中,遇到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局的局長Steven Hepler,他就跟我說「你們要小心,我們要跟對岸簽聯合公報(817公報),對你們很不利,以後軍售可能就沒有辦法賣給你們了。」所以我返國後第二天一早,我馬上就去見蔣經國總統。這時候總統就跟我說:「你不用講了,你要去美國。」我說:「報告總統,我半年前十一月剛剛去美國。」總統接著說:「你去接蔡維屏。」我問:「為什麼呢?」總統回答:「蔡維屏連美國跟中共談八一七公報什麼都不知道,你一個人在外面就可以知道這個消息,所以我要你去美國,一定要把八一七公報推翻。」八一七公報簡單來說就是對臺軍售的質和量都要逐年地遞減,你要去幫我把公報給推翻,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我就跟經國先生說:「我不能出去,不是別的,是因為我父親身體不好,需要內人照顧。」經國先生說:「你不用講了,我已經跟你父親談過了,你父親要你去美國。」那我就沒話說。
這裡頭還有一個插曲,那個時候我的名字在美國國務院已經被畫成一個小花臉了。因為1978年12月27號,克里斯多福(Warren Minor Christopher)來臺灣,我去接機,講了一段很重的話,這段話絕對不是我寫的,我要講不會用這樣的語句,這是別人寫好放到我的嘴裡,我也沒有辦法。那個時候,沒有手機,也沒有大哥大,我進去就已經發現飛機場外面不大對,就是群眾很多。我曾經在中央的一個會中講過,談判完全是靠自己怎麼樣說服對方,取得對我們有利的結果,不是靠力量。搞一大堆人去示威遊行,只會壞事。根據警務處的調查,這些人是從中壢坐計程車帶竹竿、雞蛋、番茄到松山機場。克里斯多福和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大使兩個人都受到很大很大的驚慌,克里斯多福預備當晚就回去。後來經國先生保證他,説你的安全我負責,所以他才留下來。談判談了兩次,毫無結果,因為美國根本就沒有要跟你談判的意思,美國只留了一條路,你照我的要求辦。如果我們當初照美國的要求辦,臺灣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到美國後,朋友越來越多,他們就告訴我說,美國認為你們(中華民國)混不到三到五年(1978.12),就會被大陸吃掉,這是美國對於臺灣的計畫,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所以我去美國,先去把臉洗乾淨。首先要得到信任,怎麼樣取得信任?他們告訴我,你到美國來要低姿態,你不要天天見記者、不要上電視演講、不要談政治外交,最好談些別的東西。那我很簡單,人家要訪問我,我就打電話去問可不可以接受訪問,如果不行,我就不接受採訪,我就畫一個記號;明天,酒會有我的請帖,我就問能不能參加,如果不行我就再畫一個記號;後天,有人要請客,我就再打電話,他們回答不行。於是我畫了二十個正字記號,也就是我有一百次,美國人不讓我做這個,不讓我做那個,我都照辦。第二點是很有趣的事情,美國有一個機構叫做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在德州休士頓設立了一個監聽站,把所有美國進來和出去的國外長途電話都錄音。美國朋友告訴我:「Fred,你家裡和辦公室的玻璃窗一定要用最厚最厚的窗簾」,我就問為什麼,他說:「你家旁邊一定有車子,車子裡面一定有特定的儀器會射向你家的玻璃,你在裡面講什麼話都會被錄下來。」我就說:「好啊,我就希望他們錄。」知道我在這邊是努力改善雙方的關係,不是破壞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你不錄,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證明。如此這般,大概半年下來,美國人開始改變了,剛才說不許用雙橡園。我把雙橡園修好,美國一個駐馬來西亞的大使來問我說,他的兒子要結婚,想要跟我借雙橡園,希望能在教堂舉行完婚禮儀式後,到雙橡園辦酒會。後來,我免費供應場地,也免費供應吃的喝的。但我說:「我要警告你一點,美國政府不許我用雙橡園做外交活動,那你的客人都是國務院的人。」他就說:「Fred,你真是一個老實人,國務院的人都說,錢不點不會亮,他們之所以派我來找你,就是聽說雙橡園已經修好了,修得漂亮得不得了,很有好奇心,想要來看看,你又不請他們,所以才推我出來辦這場婚禮啊。」婚禮那天,美國當時只有兩個國務次卿,一個是管政治,另外一個是管經貿的,管政治、管經貿的都來了,所有助理國務卿通通都到了,大家都很高興。我就說:「你們現在都來了,以後我再請你們來,不要再說我做的是外交。」他們就說:「沒有啦,你做的都是增進關係,不是做外交。」他們把增進關係和外交分開。
 後來就是最重要的八一七公報,怎麼照經國先生的意思廢掉。一個是質量,你現在有的飛機是F104,你新的飛機等級不能超過現在的等級,也就是拿不到F16,什麼是量,你每一年從美國得到的軍售,是斷交的那一年是六億美金,以後只有減沒有加。等到他們對我有信任的時候,我就說Quantity不能減,你美國對於很多東西都有一個指數,隨著物價的上升,指數也有上升,Cost of Living Index,那我們的軍售也要有Cost of Living Index Adjustment。第二個是Quality,別人每一天都在發展,我們只有四十幾年前的驅逐艦,還能跟他們鬥嗎?沒有辦法鬥,一定要有新的。所以我在美國那幾年的參謀總長,是郝伯村先生,他看陸軍看得很重,他一定要M60戰車,但是拿來臺灣,我們不一定可以用,因為道路橋樑不一定能夠承擔戰車的重量,但是我替他們搞來了。817公報簽了飛機,美國不好意思賣F16給我們,就叫生產F16的公司跟我們簽合約,在臺灣做IDF,其實跟F16是一模一樣的,所有的Avionics(航電系統)都跟F16一樣;海軍都是Perry,派里級在臺灣叫成功級巡防艦(PFG)。我一樣一樣得來,我也把Quality給打破了。我在美國辦事情,倒霉的事情也是,眼淚也只能往肚子裡面吞,我很感謝我的家庭,我的內人和我兩個小孩,他們看到我臉色不好時,就知道我在外面又受了氣,就對我非常好,讓我的日子過得不錯。
後來就是最重要的八一七公報,怎麼照經國先生的意思廢掉。一個是質量,你現在有的飛機是F104,你新的飛機等級不能超過現在的等級,也就是拿不到F16,什麼是量,你每一年從美國得到的軍售,是斷交的那一年是六億美金,以後只有減沒有加。等到他們對我有信任的時候,我就說Quantity不能減,你美國對於很多東西都有一個指數,隨著物價的上升,指數也有上升,Cost of Living Index,那我們的軍售也要有Cost of Living Index Adjustment。第二個是Quality,別人每一天都在發展,我們只有四十幾年前的驅逐艦,還能跟他們鬥嗎?沒有辦法鬥,一定要有新的。所以我在美國那幾年的參謀總長,是郝伯村先生,他看陸軍看得很重,他一定要M60戰車,但是拿來臺灣,我們不一定可以用,因為道路橋樑不一定能夠承擔戰車的重量,但是我替他們搞來了。817公報簽了飛機,美國不好意思賣F16給我們,就叫生產F16的公司跟我們簽合約,在臺灣做IDF,其實跟F16是一模一樣的,所有的Avionics(航電系統)都跟F16一樣;海軍都是Perry,派里級在臺灣叫成功級巡防艦(PFG)。我一樣一樣得來,我也把Quality給打破了。我在美國辦事情,倒霉的事情也是,眼淚也只能往肚子裡面吞,我很感謝我的家庭,我的內人和我兩個小孩,他們看到我臉色不好時,就知道我在外面又受了氣,就對我非常好,讓我的日子過得不錯。
Q:以老師您長年的外交經歷,只有個性外向的人適合做外交,那內向的人適合從事外交工作嗎?有發揮的空間嗎?
錢院長:做外交工作最好是十全十美,又有外才,又有內才。對外站起來隨時演講,對內低下頭來就要寫稿子,但人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從事外交工作需要外才,也需要內才,主要就是看長官如何加以使用。例如我在美國,我的同事中有內才好的不得了,後來我們替蔣經國總統寫簽都要寫很大的字他才能看得見,這位先生就幫我寫很大的字,方方正正,厚厚的一落,我再帶回來給經國先生看。有的外才好,我在美國,我靠一位臺大政治學系民國42年畢業的香港僑生馮景江,他個子很矮,他到華盛頓任何地方都可以吃得開。我要坐飛機,他只許我在起飛前十分鐘到,他就帶我直接到飛機上去;搭火車,他可以讓我的司機把車直接開到月台,直接上火車。外交團團長都沒有這個特權,可惜他已經去世三十年了。他在華盛頓,只要你有事情有求於他幫忙,沒有辦不成的,他在代表處始終是主事,他在外交部名冊裡面都不能列名。但是我把它改成專員,變成外交官,他一直很感謝我。如果你的內向文筆好,知識淵博,你也可以幫助你的長官很多很多事情。
Q:在美中兩強的競逐之中,臺灣除了當美國的扈從,是否能在兩強之間取得平衡?如果錢院長還是外交部部長,會如何制定現今臺灣的外交政策?
錢院長:基本上,外交就是交朋友,我小時候是在上海長大。上海人有一句名言:「朋友多一個好一個,冤家少一個好一個。」千萬不要製造敵人,製造敵人就是自己害自己,要交朋友,每一個國家我們都要跟他們做朋友。我在外交部長的時候常常去歐洲和東南亞,這些國家跟我們都沒有邦交,我常常可以見到他們的總統、總理、部長。但是有一個前提,我絕對不把大陸的臉皮撕破,以小事大,要有智慧,以大字小,要有仁。因為我們比他們小,所以不能做讓他丟面子的事情,我所有做的事情,都不會傷害到他們。我做部長的時候,聯合國的秘書長Boutros Boutros-Ghali,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面,但是如果你們看我的回憶錄第二本,埃及有一個新大使到華府,下了飛機就打電話到我的辦公室來,就說要來看我。我就跟他說,你應該打錯了吧,你應該要找的是PRC的大使館。他說:「沒有,我就是要找中華民國的大使館的錢大使。」我說:「你一定不要來我這裡來,對岸一定有人在我們的館外照相,你一個使字牌照的車來,你就會出問題。我願意去華盛頓最貴的餐廳吃飯,那裡老共一定不會去,因為價錢太貴了。」他就告訴我為什麼要見我,他說:「我離開開羅之前,去見外交部長Boutros Boutros-Ghali。他說你到華盛頓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見錢復,因為在華盛頓做Lobby做最好的就是這個人。」他問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說:「因為我只有朋友,沒有一個敵人,所以我到任何一個場合去,沒有人會看我不開心。所以你要想辦法交朋友,朋友越多越好。」這是今天我們最好自處的方法,盡量地交朋友。在Boutros Boutros-Ghali做聯合國秘書長時,為了讓我們重返聯合國,我不得不去看他。他告訴我很簡單的一句話:「你從臺北到UN最短的路是經由北京,只要你把北京的毛摸順了,我馬上就可以讓你們當觀察員(除了No-voting right之外,剩下的權利都跟會員國一樣)。」
Q:請問您給現任駐美代表蕭美琴女士有什麼建議?
錢院長:每一個人的做法不一樣,我的作法她不一定會照做,但是「廣結善緣」四個字是最好的方法。
Q:我們知道您從政四十多年來,歷任多項公職,每任內都有很好的績效和評價,如果未來希望從政或擔任公職,需要培養哪些技能?

錢院長:從政是為同胞服務最好的一條路。但是從政有第一個前提是,無慾則剛,不要求名不要求利,尤其利要避免,名逃不掉。我自己做了六個不同機構的首長,這六個機構我都有不同的作法,我曾經擔任過新聞局長、外交部長、駐美代表,那是獨任制,我自己要負全部的責任,所以我對於自己的要求非常嚴格,當時同仁聽到我的名字會怕,因為我會罵人罵得很兇很重。我在這裡透露一個小秘密,罵人不是好事,我在外交部的辦公室有一個血壓計,當我罵完同事,我就會去量血壓,上面兩百,下面一百,罵人是傷害自己。如果他沒有本事,那我就涼在那;但是如果他是有本事,但不願意發揮出來,我就要用很重的話去刺激他們,讓他們發揮出自己的本事。有人說被錢復罵過的人都會升官,其實不是如此,是他自己努力才會升官。我做了三個機關是合議制:經建會、國民大會、監察院。我自己不是獨任的首長,我是大家拱我出來做老大,所以我的頭一個任務,就是要把經建會的委員都安撫得很好,都讓他們喜歡我,一定來開會;國大、監察院也是一樣,絕對不能因為自己是議長或是院長就對下面的人頤指氣使,你是他們選出來的,你憑什麼來對他們說話,所以我每天都在議席裡面打招呼。在監察院也是一樣,監察委員有事來我一定在,而且一定請到客座,一定是坐在沙發上,有什麼指教,那我來請教;或者有問題,我就來解答,然後他就會開開心心地走。所以做合議制和獨任制的首長完全不一樣,獨任制那一套到合議制要不了三天就下台了;合議制的那一套到獨任制,那這個機關也一定是亂七八糟。
Q:因為您擔任過三個獨任制、三個合議制的首長,您也在您的回憶錄中提過,您在擔任經建會的主委時特別有成就感,收穫很多。很多人如果沒有仔細讀您的回憶錄,應該會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外交應該是您比較擅長的領域,那為什麼會是經建會呢?
錢院長:經建會就是現在的國建會,就是把各部會送來國家建設相關的案子先做篩檢,看看可行性如何、看看有沒有通過環評篩檢、看看國家經費能不能支應、看看工程人才夠不夠,所以經建會做的事情都是可以讓老百姓感受得到。我就舉幾個例子,頭一個例子是五股到汐止的高架道路,現在是汐止一直到楊梅,這個高架道路想法是我的想法。因為我一九八八年八月從美國回來,飛機下來,上了高速公路,就是停車場,動彈不得。我想這還得了,高速公路用了這麼多土地,只能有少數的車子過了,這是不對的。我就想起我在美國讀書,從紐約到紐澤西,George Washington Bridge,有上面一層下面一層。我請教專業的工程師,我們這邊有颱風有地震,那個東西能不能做得出來,他說我替你計算一下風速、地震強度,算完的時候告訴我說可以,但是不能像George Washington Bridge一樣,一個上一個下,但是可以架高再架一層。所以今日五楊高架橋通了,我看到五楊就覺得很開心,因為走得飛快,不會變成停車場。
 第二個就是,現在大直是基隆河截彎取直得到的,正巧我做經建會主委頭一次主持的委員會就是截彎取直案,截彎取直案的時候,炒地皮炒得不得了。我就邀請水利專家,詢問截彎取直在水利方面是否可行。他說水有親水性,截彎取直的地方不是太大,應該不至於有很大的問題。我說你等一下開委員會就把親水性提出來,現在有專家表示意見,這個案子就擱置一下,不是說擱置就不辦,會再邀請全球的專家來幫忙研究。那時候臺北市的黃市長、秘書長和局長三個人就來罵我,什麼事都不懂的人來做經建會,就把截彎取直給取消。我這一擱置,他們就認為不會辦,我就請劉肖孔博士,一位很有名的水利專家,幫我找各國的水利專家,親自來看截彎取直可不可行。結果八個專家中,四個說可行、四個說不可行。我就想起小時候住在福州街,我們家是五路公車,這個公車最後到一個水利工程實驗室。我就去問相關人士,拜託照著基隆河大漢溪一路下來到出海,做一個跟原本一樣的水工模型,經過一段時間,我就邀請立法委員、市議員、當地區長、市政府官員、里長、記者大家來看,現在是沒有截彎取直,兩百年的洪水從上面下來,以現在的堤防沒有事;如果是直的,也沒有事。這下這三個人就異口同聲地說主任委員真英明,所以很有成就感,現在基隆河截彎取直,大直開發得如此順利,所以我對經建會念念不忘。
第二個就是,現在大直是基隆河截彎取直得到的,正巧我做經建會主委頭一次主持的委員會就是截彎取直案,截彎取直案的時候,炒地皮炒得不得了。我就邀請水利專家,詢問截彎取直在水利方面是否可行。他說水有親水性,截彎取直的地方不是太大,應該不至於有很大的問題。我說你等一下開委員會就把親水性提出來,現在有專家表示意見,這個案子就擱置一下,不是說擱置就不辦,會再邀請全球的專家來幫忙研究。那時候臺北市的黃市長、秘書長和局長三個人就來罵我,什麼事都不懂的人來做經建會,就把截彎取直給取消。我這一擱置,他們就認為不會辦,我就請劉肖孔博士,一位很有名的水利專家,幫我找各國的水利專家,親自來看截彎取直可不可行。結果八個專家中,四個說可行、四個說不可行。我就想起小時候住在福州街,我們家是五路公車,這個公車最後到一個水利工程實驗室。我就去問相關人士,拜託照著基隆河大漢溪一路下來到出海,做一個跟原本一樣的水工模型,經過一段時間,我就邀請立法委員、市議員、當地區長、市政府官員、里長、記者大家來看,現在是沒有截彎取直,兩百年的洪水從上面下來,以現在的堤防沒有事;如果是直的,也沒有事。這下這三個人就異口同聲地說主任委員真英明,所以很有成就感,現在基隆河截彎取直,大直開發得如此順利,所以我對經建會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