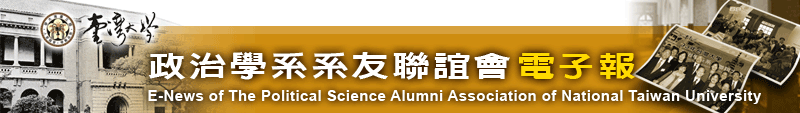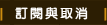歷史最前線:專訪史丹佛大學胡佛中心東亞部主任林孝庭系友
採訪整理:陳賀煦(政研碩一)

林孝庭學長小檔案:1994年畢業於台大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1997年自政大外交所畢業,2003年獲牛津大學博士。自2004年起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任職,2010年接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部主任。主要著有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1928-1949 (中譯本書名:《西藏問題:民國政府的邊疆與民族政治 (1928-1949)》)、Accidental State: Chiang Kai-she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Taiwan (中譯本書名:《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等中英文專書與期刊文章數十種。
問:首先,我們代表系友會歡迎學長回到母系,副會長張佑宗主任因今天另有會議,請我們代為向學長表達熱烈歡迎。也謝謝學長為本系與高研院在線上主講《解密史料中的冷戰與中華民國》這個重要的主題。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學長雖然就讀的是政治系,但後來的學術歷程、今日的成就都是歷史學,中間轉折為何?
林孝庭學長(下稱「林」):我在台大政治系讀公行組時,對國關組的課比較有興趣,當初一度也想轉組,但因為母系課程可以互通,所以就沒有轉。但一些國關組的課我都修了,包括李鍾桂老師的國際公法、包宗和老師開設的博弈理論、美國外交政策、還有吳玉山老師的課等等我也去修了。畢業之後,我曾一度想考外交官,因此報考了政大外交所。之後突然對於「把外交跟歷史結合」感到很有興趣,那時候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李恩涵在政大教中國外交史,從那時候起,我對「以資料、檔案為基礎的中國外交」感到非常有興趣,以後便慢慢轉到近代史的領域。畢業並服兩年預官役後,幸運申請到英國牛津大學就讀,轉而以「結合檔案與史實」為我日後主要的研究途徑。
問:因此學長外交所畢業以後沒有去考外特?到英國之後念的是什麼系?國際關係史嗎?
林:是的,我後來沒有考外特。在讀研究所的三年中,我就立志取得一個博士學位。但在系所方面,後來我申請到的其實是牛津的「東方學部」(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以研究漢學古典文獻為宗旨,而非「近代史學部」(Faculty of Modern History),我申請錯了!我那時候以為只有東方學部才能做與中國近代相關的研究,但其實我應該申請的是「近代史學部」。因此,我硬生生接受了我原本不感興趣的漢學訓練,研究古典、古籍,還要做翻譯的訓練。但這可以說是「因禍得福」(bless in disguise),因為有那幾年漢學、古文的訓練,奠定了我後來到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面對浩瀚史料的基礎。
問:學長後來在漢學系畢業的博士論文,主題為何?與歷史有什麼關係?
林:在經過方法論(methodology)的訓練後,我博士論文的主題是以「1949年以前國民政府的邊疆政策」作為主題,並以「西藏」作為個案研究。這也是為何我後來涉略到中國的邊疆研究,包括您問的「坎巨提」問題。在寫論文期間,我在大英圖書館的「東方館藏」中,蒐集到許多當年英國人在印度、西藏、新疆等等中國邊疆活動的檔案,也配合我也在英國倫敦的「國家檔案館」蒐集到的英國外交部檔案,使我能夠做相關研究的延伸。為何我選擇西藏?原因在於在近代中國中央政府孱弱、帝國主義勢力範圍廣闊的情形下,「邊疆」與少數民族議題名義上是內政議題,其實是需要透過外交處理的,例如西藏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東北是日本的勢力範圍,而新疆與外蒙是俄國的勢力範圍。要研究當時的「中國邊政」,不能忽略外交。實際上名義的「邊疆」議題、少數民族議題,其實也是外交史,是外交議題。
問:學長在讀了外交所以後改變了志願,想要做歷史研究,但台灣大部分的學生選擇留學的地點時,首選是美國。同樣是英語系,學長為何選擇申請英國?又如何到美國工作?
林:這有兩個原因。首先是,一來是我擔心GRE的成績不符預期,我的數學不太好,因此害怕去考美國的入學考試。而英國當時只需要一個TOFEL的成績,再加上當時政大一些老師是畢業自英國的,如唐啟華老師。他們給我的建議是「不一定要去美國,也可以去歐洲」,因為台灣許多都是美國訓練出來的,去英國也許可以體會到「師徒制」、「通過研究傳承」(by research)的傳統,因此我進入了牛津大學。當時有一個想法是「趕快在英國拿一個學位,然後回到台灣工作」,結果時空變化,我來到了美國──我在想,如果我當初就有意到美國學術界工作,我恐怕根本就不會去英國求學,因為學術的分工系統一般是很清楚的,在學術的連結(connection)方面,較少歐洲訓練出來的博士能夠到美國學術界來服務。
 後來,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所找到一個「博士後研究員」一年的工作,並利用那一年的時間,將我的博士論文整理並出版。其實,當時我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已經另外找到一份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但在2004年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的「中國近代史」計畫開始啟動,包括國民黨黨史、孔宋家族檔案、兩蔣日記等等,他們急需歷史研究的學者幫助該館整理檔案、研究,因此找上我。他們告訴我「當初許多年輕的大陸年輕學者也躍躍欲試,但後來都打退堂鼓──因為大陸學者多不熟悉繁體字。」後來他們認為我較適合,我就留了下來,至今將近20年。我十分感慨的是,人生中充滿各種偶然:我根本沒有在美國求學,遑論工作的計畫,可是最後我卻在美國一待待了20年,沒有返台工作。
後來,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研究所找到一個「博士後研究員」一年的工作,並利用那一年的時間,將我的博士論文整理並出版。其實,當時我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已經另外找到一份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但在2004年史丹佛大學胡佛檔案館的「中國近代史」計畫開始啟動,包括國民黨黨史、孔宋家族檔案、兩蔣日記等等,他們急需歷史研究的學者幫助該館整理檔案、研究,因此找上我。他們告訴我「當初許多年輕的大陸年輕學者也躍躍欲試,但後來都打退堂鼓──因為大陸學者多不熟悉繁體字。」後來他們認為我較適合,我就留了下來,至今將近20年。我十分感慨的是,人生中充滿各種偶然:我根本沒有在美國求學,遑論工作的計畫,可是最後我卻在美國一待待了20年,沒有返台工作。
問:學長現在待的單位,幾乎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故宮」。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學長以史料為基礎,在研究中接觸到許多冷戰、近現代的國際關係的一手素材,完成了諸多重要的中、英學術著述。然而,在你所工作的美國的高校中,國關大多採取「科學主義」(scientism)的態度,亦即他們相信凡事必有律則(lawlike)、不相信「偶然」的作用。這種學科信仰多少造成了人文與社科鴻溝距越來越大,你怎麼在美國這樣一個強調「假說」、「律則」、「實證」、「模型」的國家與國際關係學界對話?學長學掌握有這麼多有如「核子武器」一樣的史料,學長會如何向對國際關係有興趣的學弟妹們介紹歷史與科學這兩種不同的途徑?
林:在我所留學的英國,學術界非常強調歷史,甚至過度強調歷史,可能因為他們有一個光榮、悠長的歷史(笑)。像我一次來到英國的書店,光是有關歷史的雜誌就非常多,家族史、系譜學 (Genealogy),或是研究家族的紋章等等,這些刊物在台灣根本就不可能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下薰陶,就算在國際關係此一領域,許多學者也都注重史料。如牛津著名的國際關係學者傅若詩 (Rosemary Foot),他們的研究都有很堅實的史料、檔案為基礎。對他們而言,有史料,可以更有一個歷史縱深。到了美國以後,確實能夠感受到鴻溝之大,美國的主流研究完全是計量的。他們一般不重視檔案、日記,或是最多將文本數位化,去計算字詞出現的頻率,再進行驗證。坦白說,這樣寫出來的成果受眾少得多。在美國,歷史學界與這樣的量化研究,確實比較難對話。
我要強調,歷史、人文領域的東西,確實任何人都能有興趣,不論是醫生、工程師都能有興趣;而政治科學方面,讀者可能就比較小眾。不過,歷史要做得好、讓人來讀,壓力也是很大的,不但要基於扎實史料的,同時又能有超越前人的觀點,這個過程非常花時間。做為歷史研究者,我們常常也很羨慕跑程式的政治科學研究者。我們歷史研究要花三、五年爬梳檔案,就算看那麼多檔案也並不保證可以寫出東西;因此各個領域其實是各有利弊的。
問:美國許多的決策層中,其實學習歷史的不少。如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都對歷史有很深刻的研究。甚至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這麼重要的理論學者,成名作的歷史分析也是相當豐富的。
林:沒錯。季辛吉的論文是在研究十九世紀的維也納會議與歐洲「權力平衡」,而在他成為決策者以後,他也將歷史研究得到的觀點應用在決策上搞權力平衡。當年許多在美國總統身旁重要的人都是學歷史的。後來我慢慢轉到研究檔案研究、歷史研究,能與我對話較多的都是歷史學家。但我的感覺是,基於史料檔案寫出專書與期刊文章,在美國也沒有遭受排擠,傳統的政治史、國關史途徑,仍然可以在國際關係領域生存。我寫的《意外的國度》也被哈佛大學接受,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因此我相信如果內容夠新穎、有趣,就算是比較傳統的研究途徑,仍然可以獲得中、西方學界的歡迎,並找到對話的對象。所以我對學弟妹的建議是,還是要忠於自己的興趣,如果沒興趣作為動力就進一步去求學,不論是碩士還是博士都會很辛苦。不論是喜歡國關理論的一套架構去分析事實,或是想做一些人文、歷史取向的研究,都可以做得到。
問:有人說後事實(post-truth)的時代可能會更輕忽史實,這對歷史研究有沒有衝擊?
林:有的。有些人或媒體或許可以擷取日記中的一小段話,然後作為標題去譁眾取寵。由於看不到前後文,這樣的做法或許可以欺騙外行的讀者,但當放到學術歷史的專業中,最終這是會被唾棄的、學術道德是有問題的。不過,所幸真正的研究者都看得出來。
問:學長最近常談的新書《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可否以此為例向我們說明,在現代研究蔣經國,對台灣的內政外交有什啟示?我們能不能說我們還活在蔣經國的陰影之下?或說台灣還衝不出「蔣經國典範」?
林:是的,儘管我的研究是採取歷史途徑的,但我個人的堅持是,我希望我的研究成果,如《意外的國度》、《蔣經國的台灣時代》,對當今內政外交的議題,還是有一些啟發。的確,蔣經國時代很多的決策至今還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以電子產業來說,蔣經國曾在日記中提到,他承認他去參觀這些電子展,看到許多新奇的東西,但他都「一竅不通」、「像一個白癡」。而在行政院長孫運璿從韓國訪問回來以後,孫也建議比照韓國設立一個「工研院」,用最好的薪水吸引專業人才。蔣雖然似懂非懂,最後決定支持這樣的建議。其實從現在來看,這些當時很重要的決策,其實都有一些偶然性。當時台灣想搞晶片研究、高科技,被許多人取笑,認為這與台灣在世界上的分工不符合──台灣被分配到的都是最勞力密集的產業,且當時台灣根本沒有這個條件來推動高科技產業。如果當初蔣經國認為這樣的批評有理,否決了這個政策,可能又沒有今日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如果他當初沒有繼續支持李國鼎、許文淵、孫運璿,我們今天可能就不會有「護國神山」。同樣的道理,講到外交或是在對美國的依賴,在讀了他的日記以後,我也看到一樣的看法:蔣跟他的父親一樣,因為深刻的民族主義的意識,不希望太依賴美國。
問:對了,胡佛典藏的蔣經國日記總共幾卷呢?學長瀏覽內容有什麼印象深刻之處?對於這樣重要而富有爭議的人物,歷史學者應如何面對「評價」問題?
林:蔣經國從1937年5月年寫日記到1979年12月,總共四十三年。其中,1948年的日記丟失了,是他在上海整頓經濟、俗稱「打老虎」的那一年。他還是有寫日記,但原件可能丟失了。我的發現是,在國家面對風雨飄搖的情況時,蔣還是希望堅持「國格」。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儘管知道台灣不能沒有美國的援助,但他也努力在外交困境中爭取最大的自主權。當然,他內心所想的,與當時國家面臨到的客觀狀況是有一段差距的。即便他心中有自主、自尊(self-respect)的需求,但他仍然無法改變美國要拋棄台灣、與中共建交的事實。他只能考慮如何替台灣爭取更多時間周旋。但形勢比人強,台灣有求於美方多;從日記中,可以理解當時蔣心中的無奈、悲憤與掙扎。
有人批評蔣經國是「獨裁者」、「威權」;也有人懷年蔣經國的美好時代。但我要強調的是,政治人物,尤其是領導者,對於其的評價一定會是分歧的,不論正面或者負面的評價,我們都可以理解並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但無論如何,評價一個政治人物,一定要將其置於當時「特定的時空脈絡」中,而非用現在的標準,才會比較客觀。否則如果用現在的觀點去看古代帝王,自然每個都是獨裁且都有犯有「重婚罪」,普世價值的內容,歷史上看是會隨著時空轉變的。90年代冷戰結束以後,人權、民主變成新的普世價值。但在50、60年代時,冷戰反共的政治正確壓力是很大的,所以韓國的朴正熙、智利的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都可說是「自由世界陣營」。因此,在兩極對抗脈絡下,可以更了解當時各國時空的條件,而不會任意在「時空倒置」下審判前人。我非常注意這一方面的問題。

問:在兩岸與整個華人學界,學長的著作有很多讀者,現在也有許多兩岸學者到胡佛檔案關參考檔案。一個新的趨勢是,許多對岸的學者除了掌握大陸自己的檔案,也非常重視胡佛檔案館的資料。對於台灣未來的研究者而言,有一個擔憂是,司法上我們可以主張史料的所有權,但台灣的新一代學者似乎對這些「舊」的、「傳統」主題的興趣越來越淡。相對地,對岸的新一代研究者卻非常有興趣,最後有沒有可能導致近代中國與東亞歷史重大事件的詮釋權,變成西方與大陸學者在競爭?現在台灣有「林孝庭」,但未來不一定會有「林孝庭」,台灣相關研究的學者會不會後繼無人?這樣的「危機」學長怎麼看待?對學弟妹們有什麼期許?
答: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三年前,我前往浙江大學的「蔣介石研究中心」,出席一場該中心十週年紀念的學術研討會。在研討會文章裡,我發現他們的研究其時已經超越1949年,「侵入」進來在做「台灣的民國歷史」了。如果把他們所發表的論文作者姓名遮住,讀了之後已分不清楚是兩岸哪一邊的學者所寫的!他們的史觀開放程度,有時是台灣難以想像的。以前我們可以說他們有意識形態的桎梏、「台灣仍然領先5-10年」,但是,現在這樣的限制越來越少了,他們很多題目都可以做了。許多博士生的開題(編按:論文大綱),就已經是1949年以後的題目。我今天才收到一個廈門大學博士生的信,表示要來胡佛看1949年後台灣的檔案。他們非常積極,這對台灣學界確實是挑戰。
反過來說,如果是我們受制於意識形態,只限制於所謂「本土」為中心的歷史,卻沒辦法把成果與兩岸乃至於近代東亞、世界的變動連結起來,這樣研究會越走越窄。如果只做「與自己相關的」(related to yourself)的研究,那國際上可能重視程度有限。現實地說,這是不小的危機。
至於我對學弟妹的鼓勵,如果對政治史、國際關係史有興趣,我認為可以從台灣自己掌握的史料開始,在碩士班階段慢慢沉浸,去學習如何充分掌握、運用檔案。其實,台灣的檔案開放得很好,有國家檔案局、國史館、近史所、國防部的單位等等。先熟悉檔案,然後把視野提高到與周遭的大議題,如果有國際的脈絡,那研究會有更大的價值。接著,如果未來有興趣再到國外讀書,並運用中文以及英文的檔案優勢,慢慢就能夠培養出國際化的學者。如果越多人願意來投入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歷史,台灣在這個領域的份量就越有希望。對岸是以量取勝,只要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認真投入,人數就很驚人了,我們只能重質不重量。
最後,我再次鼓勵學弟妹,歷史研究是一個寂寞的工作,要花費很多時間與精力。但如果對此領域有興趣,我還是熱烈鼓勵你們從事相關研究。歷史研究雖然很孤獨,但那些史料靜靜地躺在那裡,透過閱讀檔案,你彷彿可以感覺到回到過去、「與當事人對話」,而且發現了別人沒有聽到的聲音。那些聲音不僅確實存在,至今都還有回音!那種爬梳史料後聽到的聲音、對過去歷史提出一番新的不同詮釋與理解,是很有回饋、很有意思的!這種從「政治學」轉到政治史、國關史的路,也是走得通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