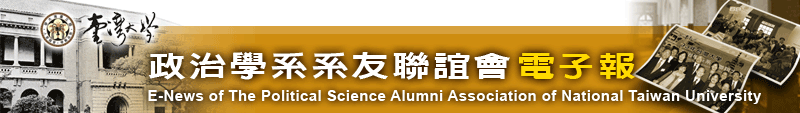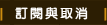新聞最前線:專訪詹怡宜學姊(77年班)
郭銘傑(92級國關組)、吳謹安(政研二)採訪整理
詹怡宜學姐(77級公行組)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姐出國留學前曾任《中國時報》,學成歸國後曾任《聯合晚報》、《自立晚報》記者,並為臺灣首個衛星電視頻道無線衛星電視台TVBS的開臺元老。學姐從事新聞工作至今約30年,歷練豐富:除了記者,還曾擔任主播、製作人、主持人。詹學姐製作的《大河戀系列報導》更於2000年獲得金鐘獎最佳新聞採訪獎;2005年學姐再以《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獲得文教資訊節目主持人獎。學姐現任TVBS新聞部副總經理,並為母校新聞研究所兼任講師。
雖然現今社會對於政治系的刻板印象是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擔任公職,學姐卻走出一條新聞路:從記者到主播,再到節目主持人與新聞部副總經理。從政治到新聞如何可能?今年3月29日下午,學姐應系友會邀請,假母系貴賓室接受總編輯郭銘傑老師、碩士班二年級吳謹安同學專訪,內容整理如下。
問:當我們還在學時,學姐已在新聞第一線服務,表現令人印象深刻。學姐在新聞的領域是一個典範性的代表人物,對於學弟妹的生涯規劃很有參考價值。想請問學姐在還有「大學聯考」的時代,是否有其他想要就讀的科系?為何會將政治系列入考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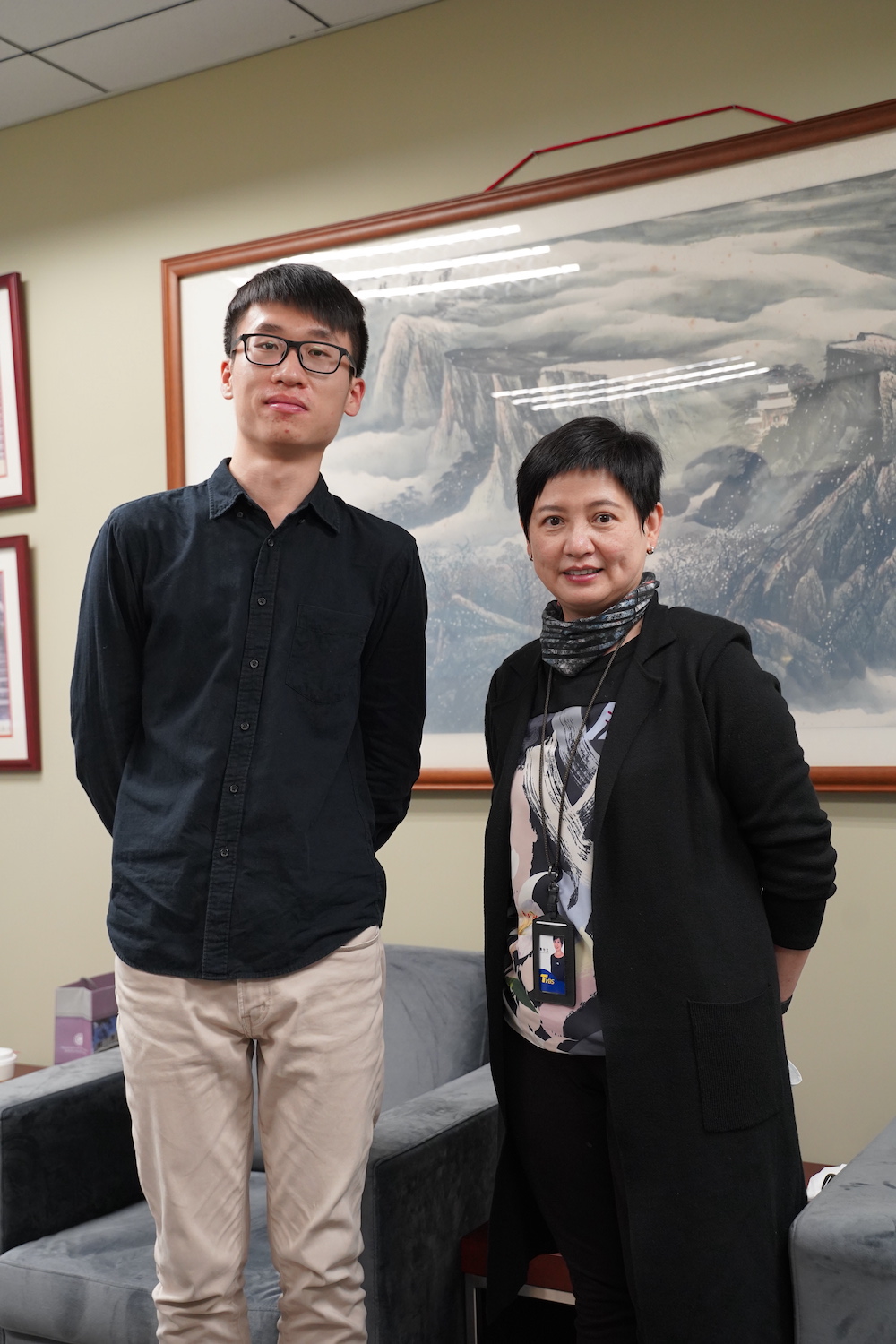
詹:我那時是就讀政治系公行組。那時是聯考變革時期,但填大學志願仍然比現在單純許多,我填志願就是照著分數高低去填。高中時,我只確定自己喜歡與社會相關的科系。儘管之後做新聞,但那時並沒有立志要成為記者,只想著自己想要做點「對臺灣社會有貢獻的事。」所以大致上還是照著上一屆放榜分數高低填志願。
當時我有填經濟系與法律系,但對於經濟,因為自己數學不夠好,所以疑惑自己是否能夠唸得好;也有一點想念法律,但卻覺得自己可能也不夠暸解法律。自己其實對於學系沒有那麼清楚,只有一個很模糊的方向。我現在看女兒未來想念法律,她會比當時的我還認真去申請。
讀政治系時,覺得最棒的出路是成為學者。當時覺得唸書是最厲害,很聰明的那種人,理應就會繼續唸下去,就是一種「有為者亦若是」的感覺,就像蕭全政老師。此外,自己也想畢業後去立法院當助理,但並沒有特別想去當公務員。
在大四的謝師宴時,彭錦鵬老師跟我們介紹了工作機會,是《中國時報》國際組的編譯。當時自己一直想著要出國唸書,但不是大四就做好準備,所以心想如果找到工作,準備一下再出國,這樣還不錯。所以我那個時候先去了《中國時報》。
時報的考試是翻譯一篇時代雜誌的文章,我的英文沒有特別好,但這個工作可以晚上上班,白天準備GRE考試,所以就到了時報國際編譯組,從那時開始接觸新聞工作。我在時報待了一年,隔年(1989年)的6月發生天安門事件,需要翻譯大量外電,國際組的同仁就被派至大陸組寫稿。那時,申請國外學校的結果也剛好出爐,我就出國了。這一年工作的經驗才讓我真正暸解新聞是什麼。雖然只是翻譯外電,但你會想像自己彷彿身在現場,覺得自己寫的東西能夠影響別人的觀點,這件事情讓我覺得很棒、很享受。我當時是最菜的,負責的是拉丁美洲的新聞,而因為拉美常發生政變,需要去暸解這個國家。剛好自己又是念政治,就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可思議。印象很深刻的是自己前一天寫的稿,隔天坐公車時,剛好看到旁邊的的乘客正在閱讀自己寫的新聞。陌生人讀自己寫的文章,讓我覺得很感動。
申請學校的結果出來,我就到了芝加哥大學讀書,過程算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在如此學院派的芝加哥大學念公共政策的那兩年,我意識到了自己如果走上學術,寫的東西可能放在圖書館,就再也沒有人看。可能是因為這樣,讓我想要做一份能夠影響人的工作。芝大的公共政策學院比較實務導向,沒有那麼的理論派。也是那兩年的經驗,讓我意識到自己沒有能力做學者。因此,在芝加哥的那兩年,讓我確定自己之後要做記者。
問:學姊在政治系時,有沒有讓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師長或是課程,以及在政治系四年的收穫為何?
詹:蕭全政老師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模式就像人生導師,很常跟我們聊天。另外,在大四時我參與了胡佛老師主持的民調研究計畫,我在裡面擔任訪員。參與的還有正在攻讀博士的陳明通與林佳龍。之所以曾想當學者,應該就是受到這群人的影響。後來我也擔任過甫回臺大任教的朱雲漢老師助理。朱老師返國寫的第一封推薦信應該就是我申請芝加哥大學的推薦信。朱老師親筆幫我寫了非常好的推薦,我才有辦法申請到芝大,讓我非常感謝。日後遇到學生希望我幫忙推薦時,我都想著要像朱老師一樣認真寫。
問:相比臺灣的高等教育,美國的訓練給學姊什麼樣的收穫?
詹:芝加哥大學的課程非常扎實。我在美國的兩年,用英文上課並理解內容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壓力非常大。本來自己是因為數學不好,所以讀政治系,但到美國卻因為自己英文不夠好,當時讓我最有成就感的課程卻是微積分,拿的分數讓我有一點自信。用英文表達讓我壓力很大,即便到現在都讓我覺得語言很重要,而語言也影響我們的思考。
研究生的課程多為討論或報告課,這是我覺得與臺大差異比較大的地方。在臺大時,大班課很多,因此那時思想訓練與表達的機會比較少。進到芝大,會很感動自己身處在一個崇高的學術殿堂。或許那兩年沒有學得非常好,反而讓我更清楚知道回國要當記者。
問:請問學姐是什麼契機,讓您畢業後選擇進入新聞界?在政治系的訓練對於新聞工作的幫助為何?

詹:從美國回來時,我寫了幾封信給報社的總編輯闡述我的工作經驗,以及自己想要跑政治新聞。但現在我在新聞界工作這麼久,卻是從來沒有收過這樣的信。當時我沒有跑過新聞,只有翻譯經驗,卻自以為可以跑政策新聞,因為念的是公共政策。這種無知的勇敢可能來自於自己念政治系,覺得政治系畢業,跑政治新聞應該會不一樣。我的認知就是跑新聞需要專業,而我具備政治系訓練的專業。
政治系的訓練讓我很關注政治話題。當時正逢解嚴,和現在很不一樣。寫了幾封信後,我收到《自立晚報》主管的回信,要我去試試看。我覺得自己在政治系受到啟發,也在意民主的發展,希望有比較開放的媒體環境。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我進入媒體,在《自立晚報》一年、《聯合晚報》一年,之後到TVBS,就這樣待了二十幾年。
問:記得那個時代「修憲」是很大的議題,是不是那個年代因緣際會的,新聞界對於政治方面的人才需求比較多?
詹:有這個可能。我覺得現在與過去跑政治新聞有很大的差異。現在媒體大多注意政黨間的政治口水,但當時我們跑政治是很重視根本性、原理性的東西,像是修憲、「委任直選」等等。當時也正值地方制度法、政黨法修法,我們會花時間討論這種「修法後影響很大的法律」要怎麼修。但現在媒體大多包裹處理政府修法過程,不注意修法細節。這種差異可能也跟我當時任職於平面媒體,跟現今電子媒體蓬勃發展不同有關。媒體從平面走向到電子,我也經歷了這一個巨變,媒體確實改變了整個社會。
問:TVBS成立在當時是很大的震撼,開創許多新聞播報方式的先河,跟「老三臺」形成很大的對比。對於現今媒體在社群網絡上的發展,學姐有什麼樣的觀察?對於記者跑政治新聞方式的演變,有沒有什麼省思?
詹:我對於使用文字表達比較有興趣,因此當時沒有特別想要進入電視臺。當時離開《聯合晚報》到TVBS,其實是想要重新思考真正想做的工作。當時TVBS剛成立,我想可以去學新的技術。當年「老三臺」新聞都有固定播報模式,政治新聞永遠擺在最前面,觀眾無法掌握當日新聞重點。TVBS重新定義了新聞的順序,是很大的突破。比如說,某地發生了大火,成為頭條新聞,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在當時是很新的嘗試。
這段時間,我也在學習如何把新聞做得更精彩,幸好老闆很支持。當時除了用SNG車播報新聞,也開始了劃時代的「2100全民開講」節目。當時,民眾call-in到電視臺是很新奇的事,觀眾也聽得津津有味。畢業幾年後,我遇到蕭全政老師,他稱讚TVBS開創了新的概念。我覺得很榮幸,改變了臺灣觀眾對電視的制式想法。當時也發生了其他重大事件,包含921大地震,覺得還好有TVBS,用全頻道新聞、以SNG連線重現新聞現場。
後來的發展,商業電視臺跳脫黨國色彩,各臺都重視收視率的情況下,節目越走越詭異,中間甚至一度比較偏向「腥羶色」。腥羶色是可以靠新聞自律去化解,觀眾也不見得愛看,因此這已經不是問題。可是政治上的口水是很難自律的,各臺為了收視率,讓立場分野越來越明顯。稍微有點藍的觀眾聽到電視臺偏藍的立場就會覺得高興,偏綠的觀眾也是一樣的道理,最後就會發現政論節目沒有辦法促進理性對話。

「2100全民開講」製作時會試圖找不一樣論點的人,做到平衡。但現在真的很難,因為不同意見的出現,可能會讓觀眾不悅。而這也跟後來的數位發展有關,閱聽人自己去找自己喜歡的同溫層,也很沒有社會力量要求節目要做到立場平衡,很難回到「某個議題應該要多方論點辯論」的時代。現在的平衡變成「頻道間的平衡」,頻道內沒有對話,這件事情其實蠻可怕的。觀眾可能覺得立場不同轉檯即可,但事實上觀眾不太轉臺,在網路上也是這樣,讓政治上的激化情形越來越明顯。電視臺的高層雖然想嘗試做理性對話的節目,但在實際執行上就是有困難,因為這樣的節目沒有收視率。其實電視是可以回到知識面,讓觀眾覺得電視還是有影響力認識一些事情,但這個過程可能是緩慢的,目前恐怕還無法看到樂觀的發展。
問:《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曾經獲得金鐘獎殊榮。想請問學姐,在走訪臺灣各地,製作行腳節目的過程中,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採訪經驗?
詹:2004年做《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節目當時,電視也是走到腥羶色的高峰,而這也是讓我們決定要做這個節目的原因。但做電視跟觀眾有關,需要看觀眾回饋決定是否繼續。在摸索過後,我們決定以講「人物」而非「事情」作為節目主軸。之後其他電視臺也推出類似的節目,才讓我們覺得人物專題是可以做的類型。總之,做電視需要一直尋找說故事的方式,得到回饋後再繼續試試看,我覺得「一步一腳印」是我們團隊運氣好,找到適合的說故事方式。而政論節目的改善之道,可能也是需要去摸索什麼樣的觀眾回饋是健康的。
而我們常說臺灣觀眾不看新聞,但這次烏俄戰爭發現臺灣觀眾其實十分關注國際新聞,所以我們才派記者去波蘭報導。而當時做《一步一腳印,發現新臺灣》,走出臺北辦公室到中南部,看一些地方的人事物時,覺得很有感觸。有一次自己曾經到臺西鄉,遇到一群小朋友,我就問他們說這裡需要什麼。有小朋友說需要百貨公司,而有一個小孩說這裡只需要「奇蹟」,當時就感覺到採訪新聞的樂趣。隔幾年回去臺西鄉採訪,會覺得有些人正做一些事,看到一點一滴的改變,就會覺得這應該算是「奇蹟」吧,也符合我們「一步一腳印」的精神。因為一則報導而鼓勵了地方上的一些人,會覺得做這件事情多少是有點價值的。而這就是做新聞有趣的地方。
做新聞時,當我們把時間軸拉出來,會發現有些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當然也有可能往不好的方向。但我覺得「時代需要被記錄」,儘管我們可能沒辦法改變,但「紀錄」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因此,在做紀錄的工作時,我都會覺得媒體是有正面價值的。
問:學姊曾經擔任過新聞界許多角色,包含主播、主持人、記者與主管,想請問哪宜個是您覺得感觸最深的,或是最喜歡的,能夠實踐自己的願景?
詹:我覺得最喜歡的應該是記者,能夠最直接訪問與紀錄。幾個星期前我在做專題時,因為人手不足而決定自己訪問、邀請受訪者,也身兼主持人。當時是去屏東,準備採訪的過程中我覺得非常愉快,開始要真正接觸人,透過影像說故事並詮釋它,是自己最享受的事情。
用影像去改變人,就像當年我在公車上看到陌生人閱讀自己寫的新聞,那個成就感是一樣的。現在Youtuber出現,電視觀眾變少,也許電視節目主持人的影響力沒那麼大,觀眾從網路上看到自己與之前觀眾大多從電視上收看,兩種感覺其實是不一樣的。我不否認,網路的出現讓媒體能夠變化的可能性變多,但我自己享受的是自己能夠影響別人,而觀眾也因看到自己的節目而受到感動這件事情。
問:政治系學弟妹畢業後有志從事新聞工作,有沒有什麼建議或是勉勵?
詹:我還是覺得政治系是非常適合做新聞的。我做記者時,覺得政治記者不需要從新聞系畢業。而我當時進媒體時,覺得只要我關心的是某個領域,則自己做記者的技術層次就不用很高,我在意的是內容。
學政治的人對政治有熱誠,做政治新聞的門檻老實說沒有很高,而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臺大沒有新聞系,而我也覺得不需要。政治系的訓練是看社會的方法,再加上你的熱忱。你有這樣的背景來作為記錄時代的人,是剛剛好的。只要再學一下用什麼方式記錄時代,不管是用筆、廣播、電視等等,做好新聞,作好一位報導者,就是貢獻社會最好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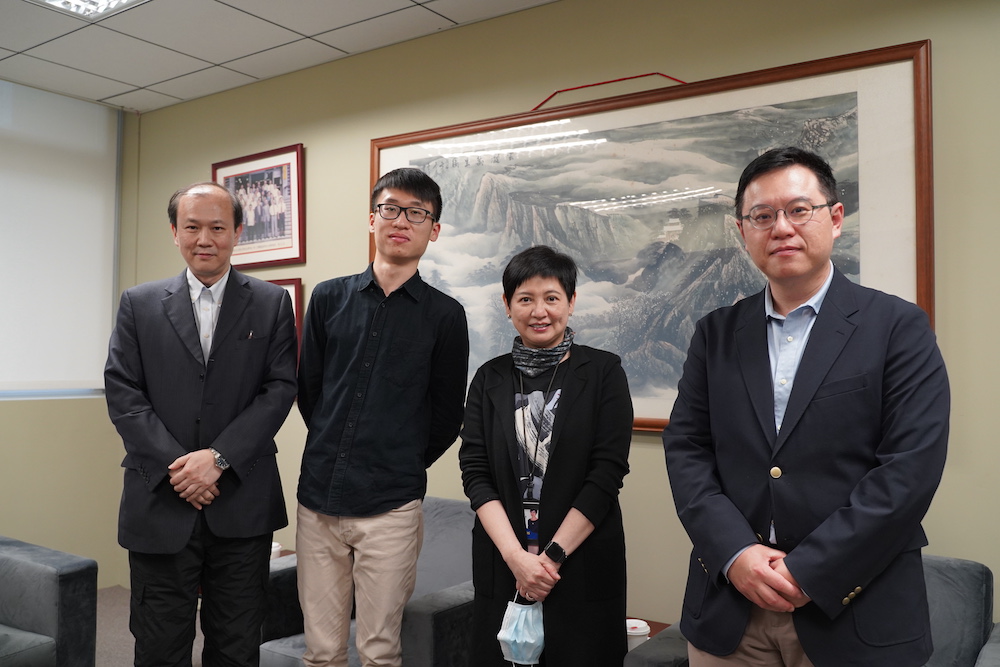
 二排左3為詹怡宜學姊
二排左3為詹怡宜學姊
 前排左2為詹怡宜學姊
前排左2為詹怡宜學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