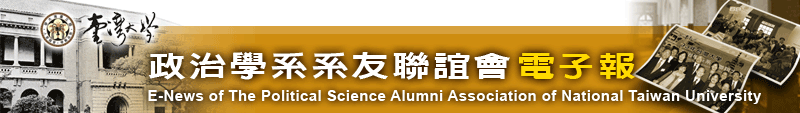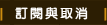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系友專訪】烏凌翔學長(EMPA13、博112年班)- 從科技媒體人到政治思想的耕耘者
文字整理/楊子蓉(政研一)
在人生的下半場,選擇回到校園重新開始,是少數人也能實踐的理想。烏凌翔學長從臺大電機系畢業後赴美攻讀工程碩士,曾在新聞及企業界擔任高階職位,亦活躍於科技評論與媒體採訪現場。五十歲那年,他決定放下熟悉的專業領域,轉身投身社會科學的世界,重新走考進臺大政治學系,展開一段歷時九年的求學旅程。此次訪談,我們邀請學長分享他橫跨理工與人文、職場與學術的經歷,並回望他對政治學的選擇、反思與熱愛。
Q1. 回到母校後,您是否有遇到比年輕時求學更大的挑戰?又是如何克服的?
 有的,而且是全方面的挑戰。體力當然首當其衝。年輕時熬夜唸書,幾乎是家常便飯。當年期末考來臨,整晚不睡,熬到天亮再進考場,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當我53歲重返臺大就讀碩士在職專班,後來又繼續念博士班時,我的身體早已無法承受這種壓力。記得為了寫論文或準備報告,我曾多次熬夜到嘴角泡疹反覆發作,像是提醒我,歲月早已留下痕跡。
有的,而且是全方面的挑戰。體力當然首當其衝。年輕時熬夜唸書,幾乎是家常便飯。當年期末考來臨,整晚不睡,熬到天亮再進考場,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當我53歲重返臺大就讀碩士在職專班,後來又繼續念博士班時,我的身體早已無法承受這種壓力。記得為了寫論文或準備報告,我曾多次熬夜到嘴角泡疹反覆發作,像是提醒我,歲月早已留下痕跡。
除了體力,還有與年輕同儕間的代溝與知識斷層。我博士班的同學多半是從大學一路念上來的政治系學生,基礎理論、名詞定義、學派分歧他們了然於心,而我雖然人生閱歷豐富,卻缺乏系統性的訓練。要與他們一同參與討論、合作寫作,對我而言是一項不小的挑戰。但我告訴自己,學術之路沒有捷徑。於是我大量旁聽課程,修習額外學分,甚至在博士班初期,每週都安排自己去補足該階段應具備的知識。這些努力說來也不足為奇,卻是我能穩穩站在這條路上的關鍵。
Q2. 您認為自己現在的學習方式,與年輕時最大的不同是什麼?這種不同對您的專業或思考方式帶來哪些影響?
年輕時的學習,靠的是記憶與拼勁;而年長後的學習,更像是一次次深思熟慮的選擇。我在念博士時已經五十六歲,無法像從前那樣靠著強記死背過關,反而更依賴理解與邏輯建構來處理知識。年紀讓我的記憶力衰退了,但也讓我對知識有更高的容忍度與穿透力。我更能辨識哪些理論背後的假設也許不成立,哪些學說雖然精緻,卻無法抵禦現實的複雜性。
我本身來自理工背景,習慣於以明確的邏輯推演思考。當年我學F=ma,知道每一個變數的意義與單位,物理與數學的清晰性讓人安心。可政治學卻不是這樣的世界,它充滿模糊、變動與定義爭議。年輕的我一度對此感到不安,甚至懷疑政治學是否真能稱為「科學」。但隨著學習的深化與歲月的沉澱,我逐漸理解:這種模糊,本身就是社會科學的本質,也是一種對人性與制度的有限描述 。
學術的成熟,不在於記得多少,而在於能不能提出真正的問題。我現在讀書的方式,是為了建立自己的觀點與思考架構,不再只滿足於知識的累積,而是追求理解的深度。
Q3. 您選擇攻讀博士的這條路,是否曾遭到家人或朋友的質疑?他們怎麼看待您的決定?
可以說,我念博士是在人生既定軌道之外,為自己畫出的另一條路。當時我剛好五十歲,從職場退休,但並沒有打算「退下來」,而是重新投入學術的懷抱。這個選擇,在許多朋友眼中是難以理解的。有人替我擔憂體力不支,有人認為成本太高,還有人直接說:「都這個年紀了,何必折磨自己?」甚至有朋友用「痴」來形容我,但我不以為忤,反倒覺得那是對我的一種讚美。
我父親過世多年,無從再論價值觀差異。但回想當年,他堅持我念理工,強調實用與就業保障。我則是在晚年,終於有機會任性一次,讀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學問。與其說是叛逆,不如說是補償。我知道這趟學術旅程不會帶來名利上的回報,但它讓我接近了那個曾經渴望知識、卻被現實延宕的自己。
當然,讀博士不只是浪漫的自我追尋。這段路極其艱辛,我前後花了九年時間,從碩士專班一路讀到博士畢業。若說這段旅程是為了什麼,我會說:是為了「看得更深,看得更遠」。那不是功利的理由,卻是最真實的動力。
Q4. 您的背景涵蓋電機、媒體、金融與政治學,這麼多領域中,哪一個最影響您的思考方式?為什麼?
我想,最根本的還是理工背景給我的邏輯訓練。電機系訓練出來的人,看世界的方式是清楚、有結構的。舉例來說,我們講F=ma,力是質量乘上加速度,每一個變數都可被定義、被測量。但當我踏進政治學的世界,我發現這裡的變數不是三個,是三十個,甚至三百個,且經常沒有共識的定義。什麼是「權力」?什麼是「國家利益」?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常常雞同鴨講。這對曾經習慣精準定義的我來說,是一種不小的知識衝擊。
 但也正是這種落差,讓我對政治學產生強烈的問題意識。我開始反思:如果政治學想要更像一門科學,它應該走向哪裡?我觀察許多社會科學學者仍停留在定性解釋的層次,對數學工具敬而遠之。我曾半開玩笑說:「政治學現在最多只能算是類科學,還不是真正的科學。」但我也相信,隨著AI、大數據、
但也正是這種落差,讓我對政治學產生強烈的問題意識。我開始反思:如果政治學想要更像一門科學,它應該走向哪裡?我觀察許多社會科學學者仍停留在定性解釋的層次,對數學工具敬而遠之。我曾半開玩笑說:「政治學現在最多只能算是類科學,還不是真正的科學。」但我也相信,隨著AI、大數據、
所以,雖然我後來走進了媒體、金融與國際關係領域,但骨子裡我依然帶著理工的腦袋。這種「理工腦」讓我在思辨中總想拆解問題、建構模型、驗證推論。它不僅影響我看世界的方式,也讓我在博士論文中試圖彌補現有理論的邏輯斷裂,譬如重新定義「國家權力要素」,並以非線性的曲線模型整合傳統國際關係的對立理論。這種跨界思維,正是多重背景的一種結果。
Q5. 您覺得政治學有什麼特別之處,讓您願意「最後選擇它」?
我常笑說,選擇政治學,是誤打誤撞——卻撞進了心裡的燈火。回顧自己從理工轉行、輾轉進入媒體與金融業的過程,人生看似順遂,卻始終有個角落隱隱在呼喚作痛:我始終沒機會真正深入社會科學。直到年過半百,終於卸下現實壓力,我才真正問自己:「那個年輕時沒追過的夢,到底長什麼樣子?」
政治學對我來說,不只是學術,而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我念碩士班那幾年,每週都像在精神上過濾自己。我會因老師課堂上的一句話而像觸電一樣興奮,會因一本理論書而整夜思索。我開始理解:政治學不是講大道理,它講的是人——人怎麼決定、怎麼鬥爭、怎麼妥協。我們以為我們選擇了制度,其實很多時候是制度選擇了我們。
這門學問讓我看到權力的深處,不只是國際上的大國博弈,而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潛伏的張力。我也才真正明白,為何自己年輕時在職場上常常「不得其門而入」,原來是因為看不見背後的權力結構。當我開始用政治學的視角去回顧過往,許多人生的迷霧也就豁然開朗了。
所以我說,政治學是一門可以幫你「解開自己」的學問。它或許無法教你致富,卻能讓你在看不懂世界的時候,擁有一點理解的底氣。
Q6. 求學過程中,是否曾有哪個瞬間讓您覺得「啊,我真的來對地方了」?
有一門課,讓我印象極深。蕭全政老師在我們碩專班的第一堂課,開宗明義就問:「用一個字來分辨什麼是知識?什麼是智慧?」這個問題既古老又簡單,卻像一把鑰匙,瞬間開啟了我對學問的重新認識。我當時回答:「知識是不變的,智慧是常會變的。」這樣的對話,不只是哲學性思考的練習,也像是在替我的晚學人生,安上了一個恰如其分的開場。
還有一次,是在接觸「公共選擇理論」的時候,那本厚重的教科書,我幾乎整本讀完,裡面有一段提到:任何影響公共政策的人,首先想到的永遠是自身利益。我一看到那句話,幾乎脫口而出:「這不就是我們社會的真相嗎!」我還特別把這理論叫作「烏紗帽理論」,意指做官的人第一件事想的是「別砸了自己的烏紗帽」。那種被理論戳中的快感,讓我久久難忘。
這些瞬間讓我知道,雖然我是跨進這個領域的「異鄉人」,但我來對地方了。我終於找到了一個願意與之與我對話、讓我不斷追問「為什麼」的地方。對一個走過多重職涯的人來說,這種知識的歸屬感,彌足珍貴。
Q7. 年輕時與現在的學習方式不同,這樣的改變如何影響您的專業與思考?
年輕的學習像是吸水的海綿,量多、快、貪心,只求全部塞進腦袋;但年紀漸長,學習變得像釀酒,需要耐心、要發酵,更要懂得取捨。當年我念電機,只管公式、變數、推導、驗算,講求的是準確與效率;但現在我學政治,更關心「定義從何而來」、「理論能否穿透現實」,也因此,思考多了懷疑,也多了對複雜性的敏感。
這種變化也讓我在寫博士論文時,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挑了一個之前很少人討論的題目:「科技力作為國家權力要素之一」,這是我從理工的直覺中發現的盲點。傳統國際關係學者談經濟力、軍事力、資源力、政治力,卻鮮少系統性分析科技力。我認為,科技不只是支持產業,它根本是推動國家競爭力的核心引擎,是能決定未來權力格局的變數。
所以,我把國家權力視為一種 learning curve,透過非線性的數學模型來整合「權力平衡」與「權力轉移」這兩大對立理論,用曲線而不是直線來詮釋國際體系的動態。這是我晚學之路的最大收穫之一:用跨界的眼睛,看見既有理論的縫隙,再用熟悉的工具,嘗試縫補那些縫隙。
Q8. 如果讓您為母校政治系學生設計一門課程,您會想開什麼?為什麼?
我早就有了這個想法,課名叫《科技與國際關係》。我在東吳大學開過這門課,時間是週五早上八點10分。你沒聽錯,是早上八點10分,學生卻全勤、零遲到,還不休息。這代表什麼?代表學生不是不願學,而是他們太久沒有遇到一門讓他們「覺得重要」的課。
 為什麼我想開這門課?因為我們的國際關係研究,太忽略科技了。我們談中國威脅、美中競爭、歐洲局勢,卻很少真正理解「為什麼半導體成為地緣政治的核心」、「AI如何改變國安格局佈局」、「國防技術如何決定嚇阻能力」。這些問題,不僅是硬實力的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存續的核心。
為什麼我想開這門課?因為我們的國際關係研究,太忽略科技了。我們談中國威脅、美中競爭、歐洲局勢,卻很少真正理解「為什麼半導體成為地緣政治的核心」、「AI如何改變國安格局佈局」、「國防技術如何決定嚇阻能力」。這些問題,不僅是硬實力的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存續的核心。
而我正好站在這個交界點。我有理工的背景,又走過新聞與政治學的訓練,可以幫助學生搭起一座從社會科學通往科技理解的橋。我教學生什麼是飛彈、什麼是晶片、什麼是大數據背後的演算法,不是為了讓他們變工程師,而是讓他們不會在討論「技術霸權」時語焉不詳。我常說:略過科技的國際關係研究,是無法真正理解當代世界的。
Q9. 您如何看待現在年輕人對學習與求職的焦慮?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焦慮是時代的共業,不是誰的錯。但年輕人要知道,焦慮有兩種:一種是「知道自己想去哪裡,但不知道怎麼走過去」;另一種是「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去哪裡」。前者是可解的,後者需要時間,也需要勇氣。
我不太願意對年輕人說教,因為時代真的不一樣了。我們那個年代的苦是物質的苦,住大雜院、用戶外廁所,從小就學會省、忍、撐。但現在的苦是心理的苦,是資訊爆炸下的迷惘與比較,是過度選擇中的無所適從。所以,長輩常常說「你們太好命」,但我覺得這樣講很膚淺,因為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難。
但如果一定要給建議,我會說兩件事。第一,誠實面對自己現在真正感興趣的事——不必保證這輩子都熱愛它,但起碼現在是你願意投入的,那就值得去追。第二,不要太快放棄。你可以懷疑,但不要輕易否定。人若沒有一點「痴」,很難有所成。我年輕時,就是太多方向、太多興趣,結果什麼都做得還行,但也什麼都沒做出成績。
所以我現在對自己最大的懊悔,不是選錯什麼,而是「不夠堅持」。年輕人若能早點找到一條值得走的路,然後不斷往下走,即使走慢,也會走出屬於自己的深度。
Q10. 如果能對40年前的自己說一句話,您會說什麼?又或者說,這段求學旅程中,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如果真有機會對年輕時的自己說一句話,我會說:「選定目標,堅持下去,不要輕易容易轉彎。」這句話聽起來像是雞湯,但我卻是在年過六十之後,才真正體會它的分量。我年輕時涉獵廣泛,電機、新聞、金融、媒體,樣樣都碰,但也因此從沒在任何一處扎根太深。有人說這叫通才,但我自己知道,那其實也是一種逃避——每當困難來臨,就換條路走,久而久之,錯過了打通某個領域的可能。
如今回首,雖有遺憾,卻也不悔。因為那些彎路,最終也都轉進了我現在所站的位置。如果沒有理工的訓練,我可能不會用數學模型去重新思考國際關係;如果沒有媒體的磨練,我可能無法在書寫中找到準確與節奏;如果沒有金融的經歷,我也無法在課堂上舉出那些貼近現實的案例。這些支線,也許沒能成為主幹,卻豐富了我的視野與語言,讓我更能體會政治學所講的,不只是權力與制度,更是人性與選擇。
至於這段求學旅程的最大收穫,其實也很簡單:我終於有機會,去追我年輕時沒能追的夢。而且,是在完全沒有功利壓力的情況下,純粹為了理解、為了思考、為了接近某些更深的東西而讀書。那是一種遲來的自由,也是一種成熟之後的純粹。我不敢說自己已經擁有什麼思想了 ,但至少我知道哪裡有光,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
這就夠了。人不一定要在什麼領域登頂,但應該活成一個越來越明白自己為何而活的人。我想,我現在,正在路上、也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