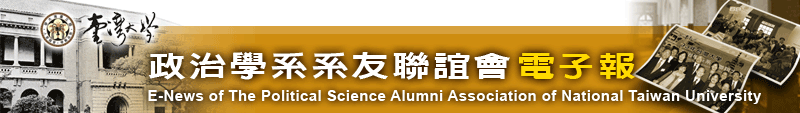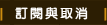新進教師專訪—郭銘傑助理教授
訪問整理/江軍(政碩四)

首先想先請問老師,一開始是什麼原因讓您對政治學產生興趣?
我一直都對政治學充滿興趣。日常生活中,小至人際關係,大至群體、部門關係,乃至國家間的國際關係,無處不是政治。為了有智慧的觀察、解釋,甚至預見不同情境下的政治互動與結果,我們需要「關於政治的知識」,也就是政治學:一門研究何人於何時、以何方法在何處得到或失去何物的學問。
所以是這個緣故讓您走上研究的路嗎?
至於研究,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一樣的。先在大學裡受到一些基本訓練,慢慢地就對越來越多之前天真地以為自然(但實則複雜的)各種政治問題產生更多的興趣與好奇心;這樣的興趣與好奇心累積到了一個程度後,也就會慢慢發現,若要將滿足自己無止境的求知欲,可能還是需要完整而嚴謹的學術訓練,也就是一個在世界頂尖大學完成的博士學位。
這個探索的過程,從來就不是汲汲營營而一步到位,反倒是有一些偶然的機緣。多年之後回想過往,大學時期的我頂多只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但並不一定了解該如何走上能通往一個自己願意投注終身熱情的工作的路。幸運的是,在我大三升大四那年,剛好現在本系的童涵浦老師、國發所的周嘉辰老師等人,還有當時大四的張立華學長等不少人都獲得美國頂尖大學的博碩士班入學許可。他們的經驗讓我在那時看到了一個自己未來的可能性。之後也因為一連串的意外演變成為今天在這裡的我。
簡言之,沒有人能夠對自己的生涯發展作完全而充分的線性規劃。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大多數人,我們總是在人生不同的時間點觀望,並且在摸索的過程中,一步步地慢慢認識自己的優點、補齊自己的缺點,而默默地走出一條路。我的研究之路也不例外。
那從臺灣到美國的學術界,這樣劇烈的視角轉換過程中,有沒有接觸到一些是您在過去從沒想過的經驗或概念?
我想在知識方面,最大的衝擊當然是:其實臺灣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重要。對我們來說,當然都覺得臺灣很重要,但若是你身處美國,特別是在美國的主流菁英之中,臺灣真的沒有我們在地的許多人想像中的重要。比方說,很多從臺灣到美國念書的留學生,總是會覺得自己是臺灣的代表,有責任和義務在海外為臺灣發聲,並進行一些幫助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的政治倡議。然而,在美國主流知識分子和菁英的眼中,臺灣不過就只是眾多國內利益競合下的一個議題(issue)而已,且它又總是非得被放在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關係中來考慮,重要性遠不如中東的以巴衝突或是朝鮮半島的南北韓問題。
至於理論與方法的訓練,還有師長及同儕的素質,自不在話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提供的計量方法訓練還有評估研究貢獻的社會科學美學是世界頂尖的;而師長與同儕也都不乏絕頂聰明、身懷絕技但又無比努力之人。很多課堂上教授的理論與方法我之前都未曾在臺灣接觸過,全部都是成為研究生以後才開始學習的。也因此,回來臺灣任教後,我一直覺得自己有義務竭盡所知,把世界上最前沿的理論、方法還有社會科學知識的美學傳授給我自己的學生。

能請老師稍微談一下您的研究領域和關注的議題嗎?
我想,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就是政治議題。如果你今天想做一個政治學者,必須要能看透各類議題之中的政治本質為何,或其中某群人在某時,會因為某種制度安排或策略互動,而得到或失去某事物。至於要怎麼做研究,又或是要用什麼方法,你要用心理學的、經濟學的、或是像現在最新潮的,利用資訊科學的做法,並沒有什麼限制。我一直覺得政治學採取的是一個多學科的途徑,端看你的研究問題是什麼,進而借鑑於其他學科中適宜的方法。簡言之,政治學並沒有一套「定於一尊」的方法,就只看你的方法是否能達致研究目標。也因此,我個人並不會為了方法追方法,而是隨著研究問題的需求來學習相對應的方法。
回到研究議題上,我現在的焦點在於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主要關注在國際經濟整合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政治紛爭和分歧。當然這之中的定義和涵義非常廣泛,例如貿易可能導致對食品安全的疑慮,抑或是經貿往來可能衍伸出的海疆劃界問題,甚至是因為訊息流通而致使人民對選舉結果提出質疑等等。以上種種都是隨著國際經貿的整合過程中,商品、貨幣、資本、人員、或是訊息流通狀況的改變,最終導致一系列的傳統與非傳統政治分歧。這些政治分歧的根源為何,又該如何被化解,我覺得這是目前全球化研究議程中最核心的研究主題,同時也與臺灣正在浮現的種種政治分歧高度相關。
我注意到老師在研究政治分歧時,是將影響分歧的因素歸結為兩類:一是制度(institution),二是領導者(leadership)與菁英(elites),能否請您談談這兩類因素是如何影響政治分歧?
從每天的新聞中,我們不斷見到各國領導人的互動狀況。因此,大家心理上總是相信領導者互動會對國際關係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然而,實際上,大多數的國際關係理論與比較政治的學說都只側重制度而對領導者少有著墨。
這當然不令人意外,因為從《聯邦黨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以降的西方政治學訓練就是不相信領導者會自我節制權力使用,而強調加諸制度制約的必要。這點我感受特別深,因為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從九零年代以來便是美國政治學專攻政治制度研究的大本營。然而,當我在上完二年博士生的核心課程後,深刻感受到,儘管有著制度約束,很多時候領導者還是會想盡辦法打破制度約束,以獲得他們想要的政策結果。看看現在川普主政下的美國就是一個最極端的例子。
事實上,政策要被制訂與執行,需要人的知識和專業,而制度本身並不具備這些東西。另一方面,政策常是不同意見間彼此折衝的結果,這也不是單純由制度所決定的。很多時候,當領導者換位,新領袖的想法和特質就被她或他任用的人帶入到體制當中去,可是制度卻一點也沒有改變,這就完全不是制度分析所能處理的。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承認,要針對領導者對政策的影響進行完美的因果推論十分困難。比方說,幾乎很少研究者能直接與領導者接觸,更別說是進行深度訪談;如果我們使用回憶錄與公開訊息進行跨國分析,又很難將其他會經由影響領導者而間接影響政府施政的干擾因素一一剔除,而找出領導者個人的獨立作用。不過,也正因為有挑戰,深入研究而能獲得突破才格外珍貴。
您適才提到了實證分析在領導者研究中的困難處,這讓我想起了前些日子讀到一篇分析,是以資料科學的手法分析白宮重要人士的推特(Tweeter)習慣用詞,並藉此來推估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所刊登、批判川普的匿名信,其可能作者是誰。從這個例子出發,您覺得資料科學方法是否提供了一個在一般訪談和統計分析之外,進行領導者研究的可能?
以你給的這個例子來說,其實它並沒有給我們太多啟發。實際上,這個資料探勘(data mining)的結果,跟一個跑白宮多年,擁有許多消息管道的記者所寫出來的猜測文章,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也就是說,他們都面對著一個黑箱(black box)、分別去建立模型、再藉可獲得的資訊去拼湊出作者可能是誰。
若要回到資料科學對研究的影響來談,我認為它還是有很多問題等待被解決。舉例來說,我們常藉由爬蟲技術來取得資料,然後宣稱這就是大數據。但重點是,就統計推論而言,你的母體到底是什麼?是批踢踢上的鄉民嗎?假設網民的數量真的那麼多,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天天上批踢踢的板上發表文章,讓你能夠取得這些訊息?若這些訊息真是你的資料來源,那麼每天發表文章的總數量都不一樣,代表母體本身不斷在變動,那這不是和統計推論假設的母體恆常性相違背嗎?
從這個例子上我們就能見到,資料科學模型只注重預測結果是否準確,但若把模型整個拆開來,會發現過程中有太多問題需要被釐清,而目前並沒有辦法處理它們。如此看來,傳統的研究方法不見得會受到資料科學方法所影響,反倒是這些新興方法會受到傳統研究方法質疑,只是因為受限於國家政策、產業需求還是社會期許,以至於現在政治學者忙於技術層次的追趕,甚至沒有時間思考這些高門檻的技術應用會產生那些推論問題。
當然,我個人並不排斥將新穎的資料科學方法導入政治學。前提是研究方法切合研究問題的需求,而不是反過來,為了應用這些看似新潮的方法而本末倒置地去進行很多耗費時間、勞力、精神,但是卻對於政治知識沒有太多推進的問題上。也唯有如此,作為政治學者,我們的研究才能讓我們國家或甚至這個世界的政治運作變得更好。
最後想請老師談談目前的教學規劃
這學年系上交付給我大一國際關係和大二比較政府兩門必修課的「重責大任」。因此,大概也沒有餘力在大學部還是研究所開授新的課程。要不然,我是很樂意開授一些新穎的選修課程,和系上現有的課程相互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