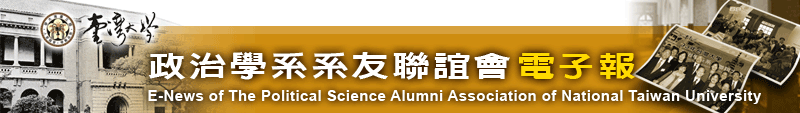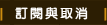胡佛院士與台灣的政治學─論超越斷代歷史與科技理性
吳玉山教授(69年班)

胡佛院士於今年(107年)的九月十日過世。他是台灣政治學的宗師級人物,對我國政治學的發展與轉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
我國政治學發展的軌跡,很清楚地是受到國際學術潮流和國內政治局勢的雙重影響。這門學科始興於民國初年,當時西方的政治學主要還是規範與制度之學,有很濃厚的公法色彩,這也反映到我國的政治學研究當中,因此政治理論、憲法與國際法等領域均受到很大的重視。民國在大陸的時期政治上頗不穩定,這也影響到政治學的發展。雖然如此,初紮根的中國政治學還是有一些顯著的發展,並且在全國百餘所大學中設立了48個政治系。
在1948年選出的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網羅了當時中國最具有學術地位的碩學鴻儒,其中便有幾位最卓越的政治學者,例如治憲法的王世杰、錢端升,治外交史和國際法的周鯁生,和治中國政治思想的蕭公權等人。這呼應了當時以規範和制度為主流的政治學傳統。此一傳統於1949年後在台灣獲得延續,但在中國大陸卻被斬斷,壓縮為馬列毛的意識型態之學。
不過,台灣政治學的發展環境並不理想,一方面是與這個學科在國外的發展潮流產生落差,另一方面就是受到國內政治情勢的束縛。二戰後的政治學開始了「行為革命」,從理念與制度轉向政治行為,在方法上也從與哲學、法學和史學的密切連結轉向與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結合,在性質上逐漸「脫人文化」而走入「社會科學」。這個「科學化」的趨勢早期在國內並沒有受到重視,使得國內和國際政治學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落差。
另一方面,台灣持續處於「動員戡亂」和「戒嚴」時期,因此凡是和國內政治直接相關的政治學領域都屬於敏感禁忌,學者踏紅線進行研究需要冒很大的風險;而非關本國政治的部門則空間較為開闊,因此國際關係、各國政府與政治、公共行政、政治哲學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可以獲得較大的發展。甚至在敏感的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也因為執政者試圖運用台灣的研究資源優勢來開展學術外交與國際交流,因而進行大幅度地開放與國際化。因此在民主化之前,台灣政治的經驗研究是最為落後的一個區塊。
在這個關鍵點上,從國外引進新政治學,並挑戰國內政治禁區的首要學者便是胡佛院士。他對台灣政治學發展最重要的貢獻便是在此。

胡院士於1951年夏考入台大法律系就讀,畢業後考取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第二期。於美國留學時是在Emory大學政治研究所,並撰寫了以「中華民國五權政體」為主題的論文。因此胡院士的早期研究是集中於憲政體制的。返台後於1961年冬季開始在台大政治系任教,一直到屆退,均教授與憲法相關的課程。他曾經與政治系傅啟學教授等六位同仁共同申請並獲得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經費補助,研究監察院的體制,出版了《中華民國監察院研究》,但這本書遭禁,研究者且被懲處,不過胡院士始終堅持關心憲政運作。
1969年胡院士獲「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獎助,前往美國耶魯大學進修,開始接觸當時流行的行為科學,特別有關政治系統、政治文化及政治參與等主題。回國後他對於治學方向做了大調整,開始嘗試在臺灣發展實證性的政治學研究,堪稱是新政治學的開山鼻祖。胡院士以臺大徐州路21號院區不到五坪的306研究室作為基地,進行研究計畫,以此培育、提攜過數十位政治學者,開花散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306的傳統後來發展成「政治體系變遷與選舉行為研究室」與「東亞民主中心」,成為台灣政治學的一個國際亮點。
引介新政治學之外,胡院士也挑戰威權體系,不斷地透過結交自由派學者、演講教學、著書立說、發行刊物、公開呼籲,和在政治勢力之間進行協調運作等方式,來推動自由化和民主化。這數十年不斷的活動,曾經讓胡院士備受壓力而且身陷險境,但是他甘之如飴,且從不屈服。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和聲望,也成為他推動政治變革的有利條件。久而久之,他成為自由派學者的主要發言人,台灣民主化的導師。在劇烈變動的環境中,各方政治人物向其請益者不絕於途。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是胡院士大展抱負的時期,當時台灣的民主化發軔,胡院士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另一方面,政治學經驗研究的風氣大開,本國政治的研究從最落後的區塊驟然上升成為顯學,並逐漸發展為主流。新穎的數量方法不斷引進、大型的資料庫陸續建構、往昔的禁區逐一突破,又與國際學術界緊密連結,台灣政治學的研究向國際化與比較化大幅邁進。一個在民主環境中茁壯、並和國際潮流接軌的政治學出現了,而這正是胡院士奮鬥數十年的目標。
從那個時候到今天,台灣的政治學持續發展,然而,就像台灣的民主政治一樣,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而與胡院士的初衷有所相違。當年胡院士為了拓寬政治學研究的視野,勇敢地跨越紅線,探索本國政治的禁區。民主化帶來了本土化,往昔的政治禁忌被打破,使得台灣政治的研究成為顯學,然而學界或是因為研究資料的欠缺、或是因為對於威權政治的排斥,對民主化之前的議題普遍缺乏興趣,好似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是始於90年代的民主化,在此之前無足研究者。這樣形成了研究議題的斷代與新禁區,造成我們無法探究制度與文化、人物與事件之間跨時的互動與聯繫,使我們對於當前政治現象的理解淺窄化。我們放棄了大量可供研究的經驗資料,歷史與文化資源,對於過去政治現象缺乏科學的理解與因果探詢,聽憑政治行為者的主觀詮釋,失去了架構與發展後進國家威權體制政治經濟學的機會,也就無法透過兩岸的比較(臺灣的過去 vs 中國大陸的現狀)來深化臺灣的中國研究(這對於台灣有「存在性」的意義)。在研究議題方面,我們突破禁區之後,自己又設置了新禁區:不僅對1949年前的中華民國斷代,還對1990年前的台灣政治斷代。
胡院士帶領政治學往實證科學的方向發展,但是他在講求科學方法的同時,從來不曾忘卻自己終極的關懷:以實踐民主來造福人民與國家。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他深深以為政治競爭所造成的認同分裂讓每一次的選舉都不是在選政府,而是在選國家,於是競爭陣營間敵我意識高漲,政治系統無由穩定,政治效能也無法達成。所以民主並不是萬靈丹,而是需要深切檢討的。然而這種規範性的自覺,卻難以在1990年代後崇尚科學方法的新政治學中出現。

量化方法的精進極大程度地增強了我們研究政治行為的能力,而且配合了由美國學術界所引領的社會科學風潮。但由人文向「核心科學」(hard-core science)轉向是有其代價的。當代的政治學除了政治思想的部分之外,一般都不處理規範問題,而是將西方所流行的價值體系視為不證自明。對於價值的探討和追求在經驗研究中匿跡,而以隱晦的前提出現。它們本身並未被論證,也因此缺乏深刻根柢。數量化的研究方法讓政治學離思想和價值的探究更遠,也更無法解答社會大眾對於政治學者所提出來的各種與價值判斷相關的問題。
在方法論單一化的情況之下,研究者不自覺地遠離了無法框入特定研究方法的議題,無論此一議題是否重大,因而使得政治學的研究與現實的需求經常不能夠有效結合。與歷史的隔絕使得政治學(包括國際關係)和史學無法相互發明,此大異於過去的傳統,也使政治學無法處理與歷史密接的議題(例如理解對岸影響世局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思想、哲學、歷史與法律脫鉤的政治學,無法從這些傳統上與政治研究密切相關的學科汲取觀點、相互豐富。新政治學在精微的實證方法上取勝,卻在倫理與規範的探究上虛無,因而看不到民主的危機,在面對危機時也只能無語。
認同政治與右派民粹主義在英美等核心的西方民主自由國家崛起,對政治學造成了嚴重的挑戰。僅是簡單地信奉形式民主、然後「就事論事」地做經驗研究便是政治學者在當下所能做的唯一貢獻嗎?胡院士所戮力以赴、辛苦經營的政治學,是要能爭取民主自由、而又免於偏激民粹,建構嚴謹科學、而又從不稍忘人文價值的「食人間煙火」的學科。胡院士的一生,是以無比的熱情,來追求民主和科學,其終極的關懷是國家與人民。這樣的精神,應該給後代的政治學者啟示:我們要建構怎樣的民主,又要發展怎樣的政治學。這些大問題,無法從切斷歷史和科技理性中求解答。